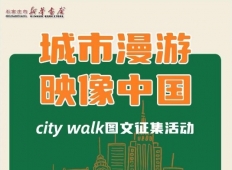六指扒着车窗说,瞎毬开玩笑,俺老汉哪有那心肠?再说老了,不中用了。见车里个个女人都戴着黑口罩,就问,戴那捂嘴子干啥?车里又不刮西北风!女人们也不搭腔,叫驴头回答,城里空气污染。六指笑着说,俺还当磨道里毛驴戴笼头,怕偷吃料豆哩!俩人瞎聊几句,叫驴头开车跑了,街道留下一股黑烟儿。
六指老远指着叫驴头骂,性你娘那屄!不就是有个当官的舅老爷吗?前几年开煤矿,赚下几个昧心钱,没几天逛窑子嫖婊子浪荡光了,如今穷得叮当响,还性个毬!
叫驴头本名叫州选,是丰腴村一个大族子孙,原本和豆镇长也是一个本族,因当年家里穷,本村老州家怕死了主人没有摔瓦盆子的人,就让州选过继给州家当了养子。州选跟六指年龄相仿,当豆镇长还是镇上一名小卒时,州选就风风火火弄那煤矿了。六指说得州选的干舅老爷叫尉郡公,就是当年在本地当县长收搜贿赂并裱糊哨马的那个人。几经迂回又当了本地和县长同级但比县长权利大的官,人称郡公公。人们拿着十八架算盘也算不机敏州选和郡公公究竟有着什么关系。州选凭着这层关系,在村北替郡公公顶缸开了一个煤口子。凭着郡公公这个硬根子,州选的煤矿开得和瞎爹的煤矿势均力敌。水塘边多嘴婆子们议论,人家是瞎虻扒在驴蛋上,扒住硬根子啦!也是恨人有笑人无。州选大婚时娶一早孕的漂亮姑娘。村民嘲讽,时也来,运也来,娶个老婆带肚来。州选家里有着似花如玉的老婆,还在外边养了好几个女人。那花销全从煤矿的成本里出。州选不喝酒还有个人模样,喝了酒老州城都是他家的。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郡公公对州选一万个不满意。哨马虽然跟着瞎爹当矿长,看着州选也不顺眼,常怀吞并之心,可没机会靠近郡公公。偏偏郡公公略通文史,儒雅派头。哨马就投其所好,联想起六指祖宗明代故事,就自称是王莽后代,学假祖宗王莽谦恭下气做派,日日往州选家里跑,跟州选称兄道弟,做着臭味相投的勾当,渐渐也跟郡公公拉上关系,也算瞎虻扒在驴蛋上,有了硬根子。郡公公对老州城历史文化也很有些研究,哨马把丰腴村一些老故事和风俗说给郡公公听。尤其把六指祖宗老话题和六指的奇闻异事倒腾几回,郡公公听了一些烂七烂八的故事,就当着宝贝来挖掘整理。又见哨马人很温顺,善解人意,就更加喜爱。说是没有历史根基和没有文化的人是弄不得煤矿的。还甭说,哨马跟郡公公来往后,断定自家祖宗姓王,因而自己也姓王。
俗话说,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用文化包装了的郡公公吃东西自有自己的风格。见哨马如此圆滑,就吩咐哨马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口号协助州选打理自己的煤矿,其用意是慢慢取代州选。郡公公站得高看得远,常以姜太公自诩,认得哨马和州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觉得哨马跟州选比起来,似乎多了一点利用价值。就耍那丢卒保车的手段,把鬼花胡子般的州选渐渐疏远。村里人嚼舌头说,看看,州选没选上,选上哨马了。恰值国家整顿私挖滥采,豆镇长公私兼顾炸毁几个黑煤窑,也不顾州选和自己有着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最后让州选顶缸的煤矿也坐了土飞机。郡公公不仅没有责备,而是拍着大腿连连叫好。豆镇长何等精明之人,趁机暗暗把郡公公煤矿版图和郡公公权属,并入自己名下,从地底下像耗子一样盗挖国家资源。郡公公并无损伤,不显山不露水,把州选踢出煤矿,依然做着袖手旁观的财神爷。
哨马顶替州选成了郡公公膝下红人和煤矿新的代理人,郡公公隐藏的更深了,成为整合煤矿经济转型的与时俱进者。老腌菜缸的故事也随之尘埃落地,渐渐被人遗忘,哨马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丰腴村。村里人又骂,这双料子汉奸可是了得!州选坐吃山空,花光积蓄,当年开奔驰,如今旧车市上廉价买一冒黑烟车子,天天拉着老婆、外母娘一家子瞎逛游。村里人说,驴粪蛋外面光。小老婆嫌寒酸一个个都跟旁人跑了。州选心里愤懑没处发泄,就在村里做起村霸的买卖。成天不睦正业,游走四方,不时敲诈一下哨马。
哨马脚踩两只船,走路比以前更摇晃了,屎肚子饕餮得滚圆。哨马搞垮州选后,他们狼狈为奸,学那托拉斯本事,垄断一方,吃掉不少小煤窑,扩大开采量,天天往京津、秦皇岛口岸等地拉煤送炭。渐渐老虎口填不满,嫌卖煤炭赚钱太慢,就想贼招儿。也是北京一国资客户老板吃了注水猪肉,突发异想,想起给煤炭里注水也一样增加分量,于是跟哨马谑说,如何如何,这般这般,俩人一拍即合,里勾外连,一吨煤加半吨水,郡公公暗中再一次拍腿叫好。豆镇长父子一明一暗,倾力支持,昧着黑心套取国家钱钞,不知弄了多多少少。后来郡公公隐退,佛高虽远,豆镇长和瞎爹依旧拜佛烧香进贡。哨马仍然做矿长不误,终于实现了他自己说的,妓女睡觉上面有人了。
如今,老州城所有煤矿早被国家全部关停并转。郡公公功成名就,干脆跟瞎爹商量,各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做老寓公去了。哨马摇身一变,也跟着豆镇长经济转型,豆镇长原位不动坐山观虎斗,哨马成为丰腴村名副其实的扶贫村长和老州城内外知名的扶贫模范。老州城一伙地痞无赖纷纷前来认祖归宗,不是亲来也是亲。
可六指根本不知道,有着当年那些不可言喻的纠葛和纷争,哨马不得不昧着良心给叫驴头以及这车里的人们都办了低保,不时也从村里账上三万两万给叫驴头弄些好处,以稳定村里局面,接三岔五堵住叫驴头的嘴巴。若是六指知道了实情,或许不办这低保、救济金,也不修这破房子,豁出老命来也要叫哨马把祖宗吃掉的那八大老腌菜缸里的银子全部吐出来。就是上法院上北京,他也要把官司打个清清楚楚。
原本六指也不把哨马放在心上,如今哨马给六指修缮了祖宅,让他住进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六指本应感恩戴德,可六指并不是这样,却又把老腌菜缸的事情重新提起,想着法子编排哨马。逢人便说,俺祖宗就知道卖老腌菜缸,也没给俺留下啥儿,还是俺哨马孙子孝顺,不仅给俺翻盖了房子,还给俺钱花。哨马偶然听说,就连老州人们一块骂,真是软奸怂毒,烂到骨子里头了!不知这话指着谁说。
看看叫驴头的金刚车拐过弯,朝大路跑了。六指就到村头小吃店里早餐。小吃店是哨马本族一个弟媳所开,不卖荞面饸饹,专卖油条豆浆,也是继承了关南老祖宗的传统。本地人一般不爱吃这玩意,都说油条不如传统的荞面饸饹好吃。荞面饸饹是老州城乃至丰腴村多少辈子赖以自豪的农家食物,偏偏六指不爱吃荞面饸饹,就爱吃油条这一口。哨马弟媳见六指前来就餐,也笑嘻嘻叫一声,六指爷爷,似乎在丰腴村,懒汉、穷汉、无赖,就是最最至高无上的人了。
不一会端上油条两根,豆浆一碗,榨菜一碟。六指牙少,只剩门牙两颗,半天咬那筋筋道道的油条,拽得老长,好不容易咬下一截,一指头塞进嘴里,却把软叽叽六指也咬住,松一下口,才把多余的软指头拽出来。
哨马弟媳问,好吃不?香不香?六指说,好吃,好吃。香,香。就把油条好处说了一通。说俺爷爷到关南跑买卖如何如何,就吃这油条和那芝麻烧饼。一个筋道,一个脆生。哨马弟媳说,六指爷爷,等俺哪天闲着了给你佬专门烤几个!俩人拉着闲话,哨马弟媳说,咱村里也有了市场经济。自古以来,村民们都是自家做饭,大清早的,出了早工,回来还得生柴火冒黑烟,累得腰酸屁股疼。
六指不知哨马弟媳说的是啥意思,却反过来说,俺就看着那柴火灶好,家家炊烟袅袅,那景致才有乡村味道。如今弄得村子不像个村子。一会又说,丰腴村老荞面饸饹,一块羊尾巴泡在汤锅里,夏天蝇子搁爬,冬天荡满灰尘,花椒粒儿像老鼠屎漂着,俺就不爱吃那玩意儿,就爱吃这油条,这并不是说,俺忘了祖宗!说着,扒拉一下软叽叽的那根多余的六指。眼见得村里大街小巷都铺了水泥路,六指站起来跺跺脚说,这光溜溜的水泥路不如咱那石头尖子铺的路面好走哩。哨马弟媳不光开了小吃店,专门伺候像叫驴头那一类人,还在村中央小广场边开了超市,伺候那些不爱做家务的年轻媳妇们,说是赚个针头线脑的小钱儿。六指背转脸磨叽,老母鸡护着小鸡,你哨马家也成丰腴村大族了。
哨马弟媳琢磨的是赚钱,可六指不知成天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俩人话不投机,一个说东,一个道西,尿不到一个夜壶里,哨马弟媳就转身到后厨里忙活炸油条去了。六指吃罢油条,四外张望,闲得无事,手无搁处,就抠牙缝里牙渍。
一天,暖阳通红。六指闲得无事,又胡思乱想起来。他不知道天上馅饼究竟有多大,心想,如今住进这宽敞明亮的大房子,老寒腿也不疼了。再过几年,还不舒服死了?不过,他住惯了透风漏雨的破屋子,总想往街道里跑。他觉得新房子憋屈,不如破房子敞豁。苍蝇也不嗡嗡了,耗子也不折腾了,倒显得万般寂寥,甚至有点气喘吁吁,呼吸都有些困难。六指自语,咱就这穷命!往日可怜惯了,如今天降大福,倒有点福寿不住了。想着想着,提溜了拐杖,拔脚就出了街门。
只见全村上下,层层叠叠,花草树林,一派金秋景象。每家房屋院墙都粉刷一新,全村上下一个颜色。六指自问,咋几天没出门村子里就变成这样了?且是秋天阴霾,村里被云雾遮盖,缭缭绕绕。六指说,就像天上宫阙一样哩!十几个村妇,摇摇摆摆,在村中小广场上跳着六指不知名的舞蹈。一个胖头胖脑看不出腰肢,一个左手六右手七,一个如鹞子翻身,一个像猿猱爬山。看得六指心花怒放,张口难合。忽见村边几栋楼房拔地而起,绿荫处还有一栋小洋楼,冒出一个尖尖,像耶稣的教堂,就问跳舞女人们,咋回事?
女人们抢着说,六指爷爷,那是土地置换,搞新农村建设,怕你这辈子赶不上,等你儿子住新楼吧!一个女人串缀说,谁谁家拆迁,得了几百万,你佬赶快去村委会,怕你家老屋不光弄几百万哩!说得六指有些心动。不过,六指自知年老,人心无拘的事情也不敢再多想了,只好悻悻说,等俺孙子们得好处去吧!六指等着女人们说起小洋楼,思谋着套些瞎话,偏偏女人们忌口,不说小洋楼如何如何。即使不说六指心里也明白,那是哨马的新居!这回六指没有扬道哨马,而是指着一伙跳舞女人说,把你们那狗腿跳断也住不上洋楼哩!
村北高处一个移民新村拔地而起,六指又跟女人们说,山汉们点几窝山药,砍几捆山柴就能过活,为啥跟咱争那吃喝?国家不如把那钱都匀兑给咱,咱就一步跨入高级阶段了。女人们听了打哈哈说,也许你佬再长一个六指或许国家就把移民那钱都给你佬了。六指骂,屁话!
忽听水塘边女人们嬉戏声儿,这里是六指年轻时常去闲坐的地方,也是他最想去、最看好的所在。顺着声音,六指穿过一道小巷,就到了水塘边。老爷庙也被彩绘一新,烂掉的砖瓦都换成碧瓦釉砖。尤其那块清朝末年本村贶秀才写的牌匾也被金粉描过。记得当年闹运动时,六指还因为贶秀才是本家一代先祖,被当做牛鬼蛇神批斗过。每每想起这些,六指心里就有些愤愤不平。今天,孙子哨马不仅给俺六指修了房子,还给俺祖宗重塑金匾,虽说那牌匾算不得什么,可它毕竟挂在了关老爷的门头上。这不仅是俺贶家的荣耀,更是俺丰腴村上下老小几百口子人的光荣。六指把这一切修缮的功劳都记在哨马一个人头上。
在六指心里不知道国家是谁。在他的心里,国家实在太大了,他看不见够不着。有人跟他说,是国家政策好,六指就说,嗯嗯,哨马就是国家。说到家传的孝悌,六指就说,哨马真是个好孙子。说到自家祖宗就骂,是那些龟孙子们卖了俺家八个老腌菜缸。
不觉走到水塘边。水塘周边早被国家投资修成台阶式的圆弧,当年长满杂草苔藓的泥泞水塘变得整齐划一。增添了几个穿着红花柳绿的年轻女人围在水塘边上,脚下一块伸进水里的石条,石条是哨马叫工匠搬掉原来七楞八柈的石头新安上的,这些规格整齐的石条是专门给女人们洗衣裳特意准备的,说是不能把丰腴村古老的传统丢掉,更不能可怜了稀罕的女人们。女人们就按着先来后到的顺序在石条上揉搓衣裳。女人们夏天弯下身腰把脚丫子伸进水里,秋天水凉,就把脚丫子团着蹬在台阶上,像夏天一样使尽全身力气揉搓那些男人们充满汗臭和污垢的衣裳。六指试图从水塘边寻找自家女人曾经用过的那块石头,转了几圈,也没找见。
一个女人就问,六指爷爷,寻啥哩?六指也不回答,一个女人指着水塘边上一块被水泥扞住的石头说,那不是?六指上台阶抚摸那块石头,上面还刻着几个小字:某某洗衣石。村里为了开发旅游,也编造了一个像“西施浣纱”那样的故事,借以填补丰腴村水塘边独特风景的精神内涵。六指觉得,最理解自己的还是水塘边浣洗衣裳的女人们了。六指感动得流下热泪。张口问说那话女人,你咋知道俺在寻找俺家女人的石头?就听见对面一个女人大声叫唤,这里是六指爷爷当年恋爱的地方。女人们听罢,哈哈大笑。六指就胡说八道,还恋爱?俺那不是搞破鞋?女人们更是大笑不止,衣裳溜水里,也不知道。
想起往事,六指目光呆痴。就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像当年一样看女人们洗衣裳。几个女人一边洗衣服,一边嘀咕着什么,不时小声耳语,不时大声喧哗,一会嘻嘻哈哈,笑得前仰后合。只听一个女人说,俺昨夜里跟男人那个什么,俺男人就像……女人还没说完,大家就笑得东倒西歪。一个女人谑说婆婆如何虐待自己,就有一个女人出来打抱不平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怨不得你婆婆。女人们听了,也没人搭腔。就有一个女人拉着哭腔说,俺那口子没良心的,夜个又在某某家打牌晚了就没回来,一个说,怕你男人跟那浪女人跑了。
另一个说,是你夜里没伺候好吧。说得大家大笑不止。还有的议论谁谁家汉子和谁谁家女人好上了,每当说起这类话题,就没人搭腔。就有女人问,今晌午该吃啥饭?有人说,红豆粥。就这话儿,女人们也笑个不停,像得了宝贝一样高兴。就有一个女人不搭话,低头搓洗衣裳,旁边女人问,咋?女人也不回答。对面一个少妇说,她夜个耍手机,男人在面弄,她没反应,叫男人扇了俩耳掴子。好大一会没有说话声,女人们把头都扭向一边。六指听得正过瘾,见女人们没人说话了,也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老爷庙前一对骚狗正在媾和,公狗身材高大,母狗个头短小。屁股对着屁股,好一阵了。女人们光顾着闲聊,也没注意,此时有一人看见,用手一指,大家不约而同看那公狗母狗交配。且是此时红日暖阳,风和日丽,两只骚狗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害羞,链住了就原地动也不动,四只眼睛各自观看不同方向的人来车往和两边景色。女人们手里衣裳也不洗了,只把双眼直勾勾看那骚狗媾和,那势头似乎比骚狗还着急。
就有一女人悄悄和旁边女人说,她大嫂,你看看,那公狗就像俺家的那个。声音虽小,早被水塘边女人们全都听见,一时愣住,稍停。哗,一声大笑,就有另一个女人站起来说,你男人有能耐,咋不叫他出来跟那母狗子试试!羞得原来说话女人的脸红到耳根,低头把衣服扔进水里。六指也不掺和,就在远处眼勾勾看那一对骚狗子媾和。
快到晌午,骚狗交配已有一个时辰。女人们和六指也顾不得吃晌午饭了。恰是这时,叫驴头老州城赶庙会回来,把车停在老爷庙前,一家子下车也凑这红火热闹。叫驴头手拿一把镰刀,老远看见六指孤零零坐在水塘台阶上面。远远挥挥镰刀叫一声,六指爷爷,过瘾吧?叫驴头指指两个骚狗吆喝。六指站起来提溜着拐杖,蹒跚着走过来问,手拿镰刀干啥?叫驴头呵呵一笑,看你佬问的,没见秋高日爽,眼看庄稼熟了,煤窑不叫开,还不叫种庄稼?羊也不叫养,牛也不叫喂,就看公狗母狗叠摞摞哩!
六指走到跟前,汪一声学狗叫。算是理解,也算回答。叫驴头也不再说话,只把镰刀在手里转来转去,打着转转。六指看着骚狗媾和,想起自己当年风流,心里烦躁,一时无名的妒忌涌上心头,对着两只骚狗猛踹一脚。两只骚狗疼得嗷嗷怪叫,只因屁股间互相链着,想跑也跑不掉,只在原地抱团打滚嚎叫,一声比一声凄惨。
叫驴头顺势把镰刀递给六指,怂恿说,有本事把那狗毬割断?六指原本闲得无事,心里空旷,眼见俩狗交配,心里早就火冒三丈,眼下让叫驴头一激将,立马夺过叫驴头手中镰刀,三步并作两步,腿也不拐了,跑到骚狗跟前,俩骚狗也是怪异,原被六指踢过一脚,早把狗胆吓破,现在见六指手拿镰刀过来,更是不敢动弹,就像人犯临刑前一样,束手待毙。六指把镰刀往那紧要处一伸,右手且是多一指头,原本没有力气的,软叽叽甩着,晃来晃去,加了助力,此时却比一般人力气更猛一筹,只听“噌”一声响,一只狗毬就割断了。
两只狗一时顾不得疼痛,分头跑开,鲜血流了弯弯曲曲两道子。且是叫驴头那镰刀城里刚刚购得,现代化淬火技术锻造,锋利无比,寒光闪闪,甭说割那狗毬,就是割那人头又有何难?只见两只骚狗没跑多远,公狗就地滚了几滚,惨叫几声,呜呼哀哉。母狗屁股里夹着半根狗毬,不知跑到何处去了,憋着牝户,怕也活不了多久。
叫驴头见了,原本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六指真个对两只骚狗下了毒手,怕大家把愤怒发泄于他,趁机驾车溜走了。倒是一伙洗衣裳的女人们不干了。大家把六指团团围住,你一句我一句,把六指骂得狗血喷头。一个女人质问说,此当二八月,正是狗狗们炼蛋的日子,你为啥把它们杀了。还有的说,你当年在水塘边不也是这样,谁也没有把你杀了?就许你搞破鞋,就不许狗狗们谈恋爱?还有的王八蛋、兔崽子等脏话骂个不停,说老六指损了八辈子阴德。狗狗也是人类好朋友,你就没一点情义?手段咋就那样狠毒?女人们一起上手,有的拽头发,有的拧耳朵。接着,女人们你一口唾沫,她一口唾沫,把六指几乎用唾沫淹了。六指没有法子,只好蹲下身子,双手抱头,被女人们团团围在中间,任凭女人们怎样打骂,也不言声,也不还手。最数那耍手机的女人打得最狠骂得最磕碜。
忽然,一声脆脆声音喊叫,六指爷爷,村长叫你到镇上领低保款、救济金哩。看看天气,渐渐暮色,女人才渐渐散去。早有村里长者远远观望,见女人们散去,悄悄捡起公狗尸体,就村外松柏林里凹处掩埋。临了说一句,世风低下,人心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