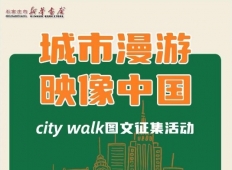不尽天雨纷纷下
(此文为国人中惰性和贪欲挽歌)
文/若愚
第五章 摆宴席毛毛媚陪酒 改名单镇长巧作弊 午餐就设在后院东厢房。人多眼杂,说啥话的都有。为的是避开众人耳目,尤其是豆镇长的俊俏模样,最是吸引女性。水塘边骚女人多,哨马怕豆镇长被她们拉下水,坏了官家名声,就把红布白纱两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因为那些翻弄口舌的骚女人们总是寻找着某种借口试图接近每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们。其实,水塘边的女人们根本没有机会跟豆镇长搭讪,再说念了科班的豆镇长跟本看不上水塘边那些骚臭女人。哨马开了顶灯,屋里也不算亮堂,昏昏沉沉。豆镇长拽拽领口说,憋死了。站起来把窗帘拉开一个缝隙,秋风就夹着香水味随着缝隙吹进来。
窗外石条路上走来一个穿高跟鞋的青年女人,豆镇长知道有人来上菜了。前院早有村民议论,这般这般,如何如何。上菜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窦毛毛。豆镇长倒是没往别处想,只是觉得窦毛毛跟哨马或可有些什么瓜葛。枣核就在外面骂那帮村夫村妇,你们就知道那点事?旁的还懂得不?
其实,经济转型后的豆镇长公务繁忙,根本顾不得美色。这都是俗人们胡思乱想的结果。或许他自己的美貌恰恰介于男女审美观的分界线上。一个镇上数万人的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柴、生老病死,都要跟他说话。近几年,国家免了农业税和各种摊派,计划生育也不搞了。人们日子好了,吃得油水多,夜里光顾弄孩子,眼见得满街撒欢的小子丫头多起来。街道两旁晒阳婆婆的老人像木偶一样摆下几溜子。因此,老百姓的大病医疗、孩子念书、青年就业、社会老龄化,都摆到镇里的议程上来。今天,在哨马家小宴一回,也是借机商讨一下村镇的工作。哪有闲工夫对女人们品头论足?
话虽这样说,可窦毛毛有着对男人不可名状的引力。那引力来源于自身的城里人没有山里人少有的天生丽质。那脸蛋说不上白净细腻,但光鲜照人,富有弹性。人说深山里飞出金凤凰,这老州城地界照样出美人。也许是男人的本性所致,豆镇长一下子就看呆了,两眼死羊眼般盯着窦毛毛,忽儿又把烟卷夹着在桌角磕一下烟灰,以掩盖自己见到漂亮女人后的尴尬。窦毛毛目不斜视,好像眼前根本就没有豆镇长这个人也似的,把一壶老酒轻轻放在桌上,又把几碟小菜摆下。回手把两个大杯斟满尚书泉酒,放在两人面前,就要踩着石条出去。尚书泉酒得名于当年藏了皇帝所赐田黄扳指的那个朝官。
豆镇长毕竟鼻子尖,扯一下窦毛毛裙角说,这是进口香水吧?嗯,法国亚菲儿Lauyfee。俺用的是维维尼奥Vivinevo。窦毛毛咯咯笑了,下意识吸吸鼻子,镇长大人也用女人香水?一句话问得豆镇长无话可说。窦毛毛说罢,跳跃一下,蝴蝶般出去。只那眼神,就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
哨马手掌在豆镇长眼前一晃,豆镇长如梦初醒。忙端起酒杯说,干!哨马开口说,镇长大驾光临,也没啥招待的。趁咱新居开工之日,俺代表丰腴村几百口子乡亲敬镇长大人一杯吧!豆镇长说,甭谢,咱们是弟兄。眼睛瞅着门口,俺也是丰腴村土生土长的子弟,不敢劳烦村长大人有此敬意。甭看哨马大字识不得一箩筐,但与官僚们相处的心机没人能比,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刚才还说些客套,见豆镇长如此模样,就改口谈一点女人。这妹子咋样?眼色猥亵,看着豆镇长表情。
此时,豆镇长鼻腔里还在使劲辨别着窦毛毛身上哪股味道是法国香水,哪股味道是她身体味道或者是她发际里的溢香。就随便回答,不错。哨马心思就等着豆镇长这句话。见豆镇长呆若木鸡,就趁机把怀中六指那个田黄扳指悄悄给豆镇长戴在左手中指上。
豆镇长如梦初醒,懂得这田黄的价值和套在中指上的用意,它的地位象征意义和求偶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经济价值意义。于是,一反刚才窘态,把女人话题换做百八正经的话题。突然说,感谢改革搞活成果吧。这话实际暗指给贫困户翻盖房屋和办低保的内容,也是哨马用田黄扳指套来的话题。豆镇长实话实说,搞活是国家的事,成果归自己。你不看,咱村文化人真是比以前多了。这话暗指窦毛毛,因为窦毛毛几句英语说得流畅。哨马说,是啊,窦毛毛就是咱村新一代文化人哩。开放搞活就得会弄几句外国话哩。哨马无话找话。说来道去总离不开女人。窦毛毛不光人漂亮,肚子里才学真不少哩!俩人谈论窦毛毛的才学,实则是品论窦毛毛的另一面。女人就是调味剂,也是一道佳肴。离开女人对于豆镇长和哨马这一类村镇干部是说不来话的。或者说女人是永恒的主题,而这种永恒早就藏在豆镇长的心底了,虽然他的言谈举止比女人更像女人。
恰在这时,窦毛毛端菜进来,放下菜肴,蜂腰肥臀,兜屁股一撴就坐在豆镇长身边。自酙一杯尚书泉,肩膀㣒㣒豆镇长,干一杯!豆镇长鬼使神差般举杯干了,豆镇长就觉得窦毛毛是多么地善解人意。看那桌上几碟小菜都是山菇、山蕨菜、山韭菜、山灰菜。水塘里泥鳅、虾米,还有市上买的鲤鱼、羊腿、猪头、牛蹄筋等都是普通但大补的美味佳肴,虽说不上多么珍贵,可在这老州城的小山村里,也是头等的讲究。这些菜肴很合豆镇长的口味。尤其是山里的野菜。窦毛毛蜻蜓点水般举杯糊弄豆镇长几下,又出去端菜,往返几回,就在豆镇长眼前晃悠。
豆镇长毕竟是一镇之长,不得不打些官腔,尽管是多年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豆镇长说,文化建设、环境保护、旅游开发很重要……但豆镇长明白哨马的用意。几杯过后,又慢慢说,搞发家致富,扶贫济困,也不能光顾这些,也要把村里精神文明一块搞上去。豆镇长忽然想起什么说,哨马啊,咱如今经济转型,文化建设,不能像以前那样张口就是屄,一说就是毬了。尤其对女人们不能说脏话。哨马笑笑,那不也是老州人几百年风俗留下的口头禅吗?豆镇长道貌岸然,一副君子派头。哨马真会见风使舵,忙接着话题说,是啊,咱村近年建了村民活动文化广场,弄了不少健身器材,女人们闲得慌,没事就到广场里跳跳舞、唱唱歌。一句话没说透,又把话题转到窦毛毛身上。
哨马说,毛毛也是大专毕业,肚里真有些猴猴哩,头几年在北京打了几年工,搞一个男人也离异了,后来就回村创业。豆镇长明白单身和猴猴的真实含义。正好窦毛毛又进来,豆镇长问,弄啥项目?窦毛毛抓抓耳朵,还没想好弄啥。豆镇长就说,回来也好,暂时没项目,就在村委会跑跑龙套吧。等有机会……窦毛毛抿嘴笑笑,机会打着灯笼难找哩。哨马说,毛毛学的是公关,外国话只是浮梢儿,也是兴趣广泛,爱好多种。将来村里搞旅游,就叫她负责联络工作。搞搞妇联都可以。
豆镇长也不加思索,随口说,好、好、好。窦毛毛干脆坐下陪豆镇长、哨马喝酒。豆镇长喝几口,抽几口烟,思考一会说,叫窦毛毛在村里干,那是大材小用。这话哨马没听懂,可窦毛毛听明白了。
女人重要,可利益更重要。尚书泉儿一直喝到阳婆婆落山。鞭炮响处,哨马打地基的机械轰隆隆响个不停,震得豆镇长、哨马、窦毛毛三人光喝酒不吃菜,尚书泉喝下两瓶子多,那鲤鱼干瞪着瘪眼纹丝没动。只把几盘子野菜吃得盘底朝天。当年城里人吃菜,村里人吃肉,如今村里人也吃菜了。而那些盛老腌菜的大缸都被村民们弃之于村外,像一个个黑老汉蹲在村外的地塄上,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向来来往往的世人们表白着丰腴村过去的贫穷和今天的富庶!也述说着人们在老腌菜缸故事中所扮演角色的历史纠结。豆镇长也不问哨马家盖房如何如何,哨马懂得,顶头上司的沉默,不仅是一种默许,对他也是一种保护。若是问个子丑寅卯,恐怕他要到纪委或者公安部门去说道说道了。
豆镇长、哨马酒喝多了,叫窦毛毛出去停了施工的机器和音响。屋里静悄悄,只有交杯换盏的声音和偶尔摸手踢脚的动作。三人喝了一杯又一杯,喝了白酒喝啤酒,喝了啤酒喝红酒,喝得豆镇长、哨马提溜着裤子不停地往厕所里跑。俩人用尽最优美的词汇,谝窦毛毛是多么海量、女中豪杰,又是多么的包容和海纳。说得窦毛毛抿嘴咯咯笑着,笑声里饱含着对今后美好前程的憧憬和向往。窦毛毛早就发现哨马屁股底下有一个打印的本子,窦毛毛知道那是一种记载什么的本子。
趁着豆镇长、哨马出去小解的机会,窦毛毛翻开本子,是个花名册。只见上面写满人名,人名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有一些陌生的字眼。在最后一行里,清楚地写着窦毛毛的名字。瞎爹、六指等和当年那几个打煤窑而如今败了家业的人们都写在第一页。还有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数十口子人等。其中或有一些不思进取、随时而过、平平淡淡、无依无靠或丧失劳动能力而致贫的鳏寡孤独老人。其中有三两个老人从解放以后就是村里的重点五保户。窦毛毛见有自己的名字,一颗久悬的心跌在肚里。
窦毛毛见自己目的已经达到,又见豆镇长、哨马酒意渐渐上来,怕他们拴不住心猿意马,再做出出格的举动,咱可不能平白无故做这样无畏的牺牲,她要把自己全部的所有一古脑儿投资到最有回报的地方。她想钻进政界的理想阶层,那里是她最最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可是,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遇,今天这种间接的偶然的机会终于到来。但今天太不合时宜。哪天有机会跟豆镇长单独那个……什么。她知道豆镇长是最适合自己的一个阶梯和载体。
哨马知道窦毛毛心里想啥,就跟窦毛毛耳语,豆镇长可不是俺当年那样,人家是妓女睡觉,上面人多着哩!知道不?豆毛毛忽眨着眼睛,揣摩哨马话里的意思。
豆镇长、哨马出去小解,久久没有回来,窦毛毛断定他们不是喝醉了酒,而是有意避开她这个局外之人另有图谋的。窦毛毛撩一下裙子,跳跃几下,逃出了她梦寐以求而又鄙夷的场所,却不知为她谋划着美丽蓝图的那个人比他还着急。
女人最终比不得利益,但女人本身也确实是一种利益。六指的田黄扳指还真起了作用。哨马搀扶着豆镇长从厕所回来,豆镇长做为上司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当年刘季在泗水当亭长的时候,也是他这么大一个小官,当高阳酒徒嗜酒如命而放荡不羁时,就是这样搀扶着刘季上厕所的。俩人互相借力回到东厢房,撩门帘一看,早不见窦毛毛踪影,哨马说,跑了,跑了。一声跑了道出多少深刻的含义。豆镇长接着说,咱可没把她怎么样!哨马说,你佬多心了,她也没把咱们怎么样。
俩人哈哈哈笑了几声。见屁股下花名册挪了地方,哨马明白窦毛毛看过了,窦毛毛名字上明显有一点油渍。他就是用这种时隐时现、愈明愈暗的方式笼络或者牵制窦毛毛的。窦毛毛离婚后,单身独居,一般工作不想干,看些闲书,涂脂抹粉,保养得嫩蕊一般,静待时机。可日子有时拮据,因为办低保,窦毛毛没少跟哨马折腾过。其实,哨马最想给人们办低保的人就是窦毛毛。冠冕堂皇的说辞是照顾人才和保护人才。可哨马根本不知,六指的田黄也起了反作用,今后的窦毛毛和从前一样,将不属于他一个人所有。
哨马把花名册翻开让豆镇长一一过目。豆镇长瞪着眼睛仔细查阅和审核花名册上的名字。六指写在第一行,三老汉、石头娃、五鼻头、大脑袋、刘翠娥和叫驴头……等和当年臭名远扬的懒汉二流子们都写在花名册上。豆镇长见写的都是乳名绰号,就问,为啥不写大名?哨马说,他们从娘肚子里爬出来,他爹就没给他起过官名!也有叫先生起过官号的,都没叫出去。豆镇长惋惜说,可惜,泱泱文化大国,连个名字也叫不出来。这不是有殇国雅是什么?哨马嘟囔,俺也没大名,有大名也叫不出去。你佬还甭说,俺连姓啥都不知道。俺爹叫牛栏,俺叫哨马。其实,哨马本姓王,那时祖宗们光顾土坷垃里刨食吃,牛栏跟他提了几回他也没记牢靠。
还真有几个有名有姓的人家,可土生土长的豆镇长却不认识,名字夹在字里行间,不甚显眼,其中牛栏也写在里面。死了几辈子的人也办低保,并不是一件怪事。豆镇长指着下面字里行间,不禁问道,王俊花是谁?哨马脸红了,嗫嚅说,白家庄俺舅爷爷的表妹妹的亲表姑。咋弄到咱村?哨马无法回答。还有一个叫韩宝贵,是黄帝城燕翅村人。豆镇长问,这也是你家亲戚?嗯,俺妻弟他姥姥家外甥的闺女女婿的小舅子兄弟。像这样的情况约有十头八个。豆镇长也弄不清农村这种炼蛋亲,拿起笔试探着划拉了几下,最后气得把碳水笔搉断扔在地下。哨马就厚着脸皮把自己的碳水笔交给豆镇长。从来不骂脏话的豆镇长骂了一句,日你娘的!口外镰刀,揽头子宽!
见豆镇长开口骂人,哨马忙把冷茶换了热茶,豆镇长呷了一口。哨马心里就想,你家亲戚也不少哩!光你那瞎爹驴毬马蛋拉耷了一大嘟噜,算起来也有十几口子,九族里怕有三族吧?你外母家也不少,三姑姑二姨姨六舅舅,都上了花名册。看看豆镇长并没有把自己的人划拉掉,就嬉皮笑脸地恭维,脑袋差不多扎在裤裆里。镇长大人真是好人,最是可怜穷人哩。比俺亲爹还亲。觉得不妥,又说,俺叫瞎爹还叫亲爹哩,说起来也是一家子人哩。豆镇长说,俺爹眼瞎心不瞎,你叫瞎爹俺可不叫瞎爹!
其实,俩人也是心照不宣。瞎爹不瞎爹,平日里咱孝敬照顾的并不多,如今国家拿钱给他们养老,说把他们包养起来也不现实,若趁着手里权势多弄几个钱花也是实在话。豆镇长又圆滑地解释,君子取财,取之有道!官场的人就是要讲套路,首先要程序合法。谁没点私心,好汉护三村,好狗还护三邻哩。这豆镇长还真能耐,这种原则问题几句话就叫他抹平了。这叫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集中统一和群众路线相结合。豆镇长诠释说。接着问哨马,开了村民大会?哨马心想,开个毬!嘴上回答,几个骨干碰了碰。豆镇长叮嘱,抓住主流,反映民意。千万叫本人签字!
审核罢低保名单,接着审核翻盖老屋的事。头一个又是六指,豆镇长笔头子厾着说,典型抓得好!其实没看清楚。下面几页也是因不同情况致贫而贫困程度都差不多的农户。哨马想汇报些什么,豆镇长摇摇头。豆镇长也不详细过问,反正国家钱已经花出去几十万,老房子旧貌变新颜,红瓦白墙蓝边麻溜清一色,明明白白的政绩摆在那里。除非没长眼睛,但凡长着眼睛能出气的人都能看出来。只是这花多少钱村民们并不知情。哨马心里明白这里头的猫腻,干瞪着眼就看豆镇长咋个样法处理。只见豆镇长拿笔头子厾嗒着六指的名字琢磨。豆镇长问,这是花了多少钱?哨马说,3000元。字迹有点模糊,豆镇长说,这3字写得跟8差不多。哨马见问,知道自己有心作弊的事迹败露,就说,改改吧,你佬知道俺没文化。豆镇长就把3字描清楚了。
令哨马万万没想到的是豆镇长在每户的花销后面都填了一个零。3000变30000,5000变50000,不由大吃一惊,善于翕合的嘴唇半天没有合上。心想,这狮子比老虎的嘴还大!狮子和老虎比,究竟谁厉害,只有天知道。哨马假意提醒,这数字都要上报的,民政和扶贫部门都要照此拨款。豆镇长听了,淡淡回答,明白。眼神坚毅,大有虎口夺食、“巾帼”不让须眉之势。随叫哨马签字画押,哨马就花名册上写下自己名字,腰间摸出村委会大印,盖了印记。豆镇长也不推诿,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签了自己官号,交给哨马说,镇上找秘书盖章去吧。哨马想起骈母枝指的“骈”字,原来豆镇长不愧是和自己站在一个壕沟里打拼的人。六指并不多余,确是一种得体的附和与并列。
办完公事,豆镇长、哨马就拉些闲话。让绷紧的神经放松一点。豆镇长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诙谐而洒脱,根本看不出他久久变态后的娘娘姿态和听不出他委婉的鸟似的叫声。他不紧不慢说起丰腴村一段脍炙人口的老故事,这个故事也是骈母枝指,跟老腌菜缸的故事一脉相承,是一块土地上的另一个版本。
说的是当年丰腴村有一供销点。两个人轮流值班,共同管理着一些日用杂货,尤以卖散装白酒利丰。散酒性烈,为了多卖钱,一个值班的往酒缸里添了几瓢水。翌日,另一人值班,又往酒缸里添几瓢凉水。每天如此,烧酒真变成清水了。村民们气愤不过,就把二人告到县里,法院判他二人掺杂使假,欺哄百姓,结果都被判了三年徒刑。哨马听了睁大眼睛问,这是哪个缺德鬼坏了良心?
豆镇长轻描淡写回答,瞎爹和牛栏。瞎爹不用说,人人知道是谁。牛栏就是当年逃荒来的老侉那个小儿子,哨马的亲爹。哨马想起来了,是有这么档子事情,当年贫农团为照顾哨马家生活,就推荐哨马爹供销点当了售货员,跟瞎爹搭档卖货。哪料这暗室亏心的事,八辈子祖宗们比别人做得并不少。雁过拔毛,老鸹落到猪背上,还有脸笑话别人!哨马手指厾点着豆镇长的后脑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