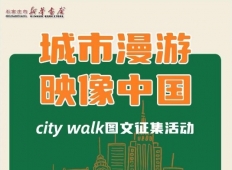不尽天雨纷纷下
(此文为国人中惰性和贪欲挽歌)
文/若愚
第二章 访贫苦哨马暗藏贼心 当爷爷六指穷耍无赖 六指心里苦闷,慢慢爬上炕头,也不管白天黑夜,拽了破被子盖在身上,倒头便睡。与其说盖着被子,不如说盖着一堆烂棉絮。懒汉觉多,说睡就睡,呼噜呼噜打起鼾来,不觉已是翌日半晌。家里拮据,六指再也没心思到破庙前看那女人们摇曳风景。恍惚间忽听堂门响动,眯一下眼睛,就看见一个黑影。爬起身子,揉揉烂眼边眼睛,见是村长。六指又躺下“嗯呀”一声,孙子来了?嗯呀,不,村长来了?六指翻翻身,叫惯孙子也当惯孙子的六指改口。那声音显得少气无力。被六指称为孙子和村长的人,是丰腴村名副其实的村长,小名叫“哨马”。其实,哨马早就在六指院里转悠一阵了。
村里人都知道,六指家藏着宝贝,可六指年轻时在水塘边和女人们戏耍时,差不多早把那堆瓶瓶罐罐讨好骚女人们了,说是都不值钱物件,让女人们拿回家放些豆豆巴西的吧,也甭到街里去买了。六指对女人们的事想得周到细腻,当年祖奶奶们几个银簪银戒也送给女人们。这些往事哨马都知道。他今天来,是受上面委托给六指修房子的,也怕那些仅剩的宝贝再落在别人手里,尤其是那只田黄扳指是旷世稀缺稀罕之物,再不能好过了旁人。其实,那些常在六指门口转悠的古董贩子中就包含哨马其人。给六指修房子也是村里扶贫重点工作,哨马不敢懈怠。顺便牵只羊,也是理所当然。
哨马空右边袖头里没有胳膊,哐当着,小小眼睛,深如蚁穴,是一个很能算计的人。当年吊儿郎当也没个正经职业,小时放羊喂驴,摲葽子铡草,掏厕所垫圈,菜地里摸瓜,牲口圈里薅毛,老太太家里捉鸡,瓦眼里掏鸟喂猫,啥事都干过。哨马斗大字不识一个,长大后,既不想种地,更不想出力,跟六指所不同的是,专门隔挤着小眼儿寻找有好处的地方投机钻营,踅摸点实惠。哨马常有口头禅挂在嘴上,啥叫好汉?拳头大胳膊粗就是好汉!心眼活泛就是能人!别人咋不当村长?俺就这点本事,才当村长哩!这是哨马和六指的最大区别。没长六指的拳头攥起来才协调,自然有力气。
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公职人员下海经商,天时地利人和,哨马占了地利。他在丰腴村人熟地熟,哪个沟沟有个瞎蝼窟窿,哪个岔岔长着棵歪脖子树,哪个坡上埋着谁家先人,谁谁当过土匪,谁谁干过响马,他都知道。哨马摇身一变,真成了“哨马”。密探也似领着政府中数个白吃干饭的人和来了一帮又一帮的地方闲杂人员包括老州城一伙地痞流氓无赖帮闲二狗油车豁子店脚牙抓街的掏腰弥的领瞎子算卦的窜门子说媒的等腰里没有几个钱而专会在街面上抓好处背地旮旯里行骗的人,唯独没有长六指的,成天价拿着蓝道道图纸在村里漫山遍野的沟沟岔岔里乱转悠,专捡煤头子厚实的地方钻那窟窿眼子,把山清水秀郁郁葱葱一个丰腴村弄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遍地狼藉。
那时哨马就是一个无赖。屁股后面常常跟着一帮喽啰打手,他们狐假虎威,互相借力,黑白通吃。哨马见天时已到,顺势而出,不管谁来丰腴村开煤窑,他都要像薅牲口毛一样,薅上两把。趁着来此抢占地盘的人们立脚未稳,霸占几道沟沟岔岔,吹胡子瞪眼,自封煤矿老板,讹诈一方。咋咋呼呼跟老早年当地的煤矿黑把头并无两样。不管哪里来此淘金的人,都得让他三分。逢人便说,俺这地盘是拼命打出来的!俺是寡妇睡觉,上面没人。俺若是上面有人,也不会这样哩。不知他上面有了人,还要成何体统!
多少年过去,哨马也跟六指祖宗们一样,昧良心钱弄了多多少少,积累得家资万贯。哨马虽然手里有钱,可贼心不死,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常常惦记着六指家那只田黄扳指。如今古董注入文化商业意义,那田黄扳指说不上价值连城,可身价也翻了多少倍。但哨马心里惦记六指田黄扳指的动机绝不是为了钱财。哨马心里龌龊,行为恶劣,可为了不惹众怒,不得不表面装得大善人一般,见了村里老人,不是爷爷就是你佬。见了后生,不是大姐就是小哥。口甜得蜜糖一般。见了上面各部门来人,也不管都是些什么玩意,杂五杂六,只要是打着政府招牌和执法俩字,哨马都是低头哈腰,卑躬屈膝,装得像一个孙子模样。哨马目的就是必求一个人和的历史局面,借以包装和掩盖自己肮脏的内心世界和斑斑劣迹。
甭看哨马对外像孙子,对矿工可是如狼似虎,常怀提防之心。动辄颐指气使不说,打打骂骂更是家常便饭,心奸到对任何人都不相信。一次到井下掌子面监督矿工作业,突遭矿顶塌陷,躲闪不及,被砸断右臂,好歹老天爷给他留了一条性命,落下终身残疾。那日枉死了几个矿工,哨马给手下几个封口费,就叫手下悄悄把死难矿工就地掩埋。自己找羊倌接上右臂,后来化脓溃烂不止,到医院截断了事。却不知神目如电,躲不过佛说的因果报应,或许哨马也是命运多舛。哨马夸下海口,今日不死,必有后福。
果不其然,神鬼怕恶人。旁人见了哨马躲得老远,可镇里县里和哨马有着臭气相投的几个狐朋狗友却视哨马为宝贝。他们渐渐浮出水面和哨马接上了关系。他们明辄称兄道弟,暗中结成团伙盗挖国家资源,视党纪国法而不顾。见哨马被煤头砸断胳膊,明摆着哨马弄不了煤矿,比断了祖宗血脉还难受。不知嗅到什么味道,几个浮在表层的幕后新贵也研究了几回,跟着撇浮油的淤渣们敲着边鼓也说,弄煤矿也不是长久之计哩,不如把哨马安排在基层,将来也有用处哩。美其名曰,哨马为地方发展立了大功,说他挖不了煤窑就叫他回村当干部吧。即使干部当不好,还不是一个绝好的“哨马”?村里就有哨马一帮无赖和老州城一帮地痞推波助澜,丰腴村人多事杂,啥人没有?没有一个像哨马这样的人,怕镇不住邪气,治理不好村子哩!
不久,煤矿关停并转,新贵们就趁着所谓的“民情民意”说法,委托年轻的豆镇长跟哨马说,村里烂事多,你要好好干哩,不能辜负领导们的一片好意。哨马因祸得福,拍着胸脯说,就凭俺这点能水,到哪里也是粪扠子掏屁股,硬手一把!如今政府经济转型,煤矿关停并转,重心转到文化旅游环保方面,叫人们共同致富,哨马就担起丰腴村大事小情,尤以扶贫为重点、中心,摇身一变,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哨马”。哨马改头换面,穿上老百姓马甲,混迹于村民之中。哨马知道,扶贫就是老辈子人说的扶危济困。咱鬼门关都闯过来了,还怕扶贫?哨马拍拍胸脯信誓旦旦,心里诡秘一笑。这都是老话。
哨马进得六指门来,心里也怀着一种愧疚。愧疚源于六指祖宗那八个老腌菜缸。哨马见六指睡眼惺忪,可怜巴巴。甭看六指炕上躺着,其实老来觉少,夜里梦多,似睡非睡,就显得萎靡不振。六指年轻时懒惰成性,如今后顾之忧常扰于心,可今个见了哨马一村之长,也知道村里正在扶贫,不由抹抹眼眦疙瘩,哼哼唧唧几声,苦菜着脸说,他哨马孙子,哎……,俺哪天怕不砸死在这老屋里?说着指指屋顶窟窿。那哭丧的可怜相,似乎是普天下最不幸的人了。偏偏屋顶雨水没有涃尽,混着老屋的污垢,滴嗒了几滴黑水。六指望望黑咕隆咚的屋顶又说,咱今天死明天死都一样!说着流下几滴老泪,那可怜相更加显得凄凄楚楚。
哨马瞅着六指哼哼唧唧少气无力的模样,心想,看见俺你那鬼难拿相儿就来了。六指浪荡多年,啥人啥事没见过?同样也会装蒜,逢场作戏不比哨马差,那懒汉手段也是了得。再叫哨马一声孙子,你看看咱这家,也不像个家哩!坐也没处坐,站也没处站。就把棉絮往炕里拽一拽,叫哨马坐下,哨马就跨炕沿边坐下半个屁股,假装万般关心,亲亲地说,你佬还是躺着吧,甭着凉了。六指就把破棉被往自己身上拉一拉,哨马也给六指往身上拽拽、拍拍,假惺惺问,怕是哪里病着了?六指嗫嚅说,其实也没大病,就是身上难耐,哼哼……嗯嗯。哨马知道六指身子没病,心里都想些什么,话儿也不往六指心里说。就说,还是叫俺哨马吧。
哨马心想,你口口声声叫俺孙子,俺就是你孙子?若是这样,俺咋给别人当这一村之长?再说,俺也不姓贶!六指可不管哨马咋想,就改口不叫孙子,叫了一声哨马。叫哨马也是俺孙子,不叫哨马也是俺孙子。六指心里说。其实,按辈分哨马真叫六指爷爷。不然,六指哪敢轻易叫一村之长的哨马为孙子?这也是延续老祖宗们一个习俗,国人里众多异姓家族,累世贫穷,老大不小娶不上老婆,辈分就大。比不得富家子弟,年幼就娶妻生子,等孙子钻出娘肚子,那穷汉早已黄土埋了半截子,新生幼儿不叫那穷汉子爷爷叫啥?还管同宗不同宗?这也是乡党间年少者对年长者的一种尊称。
不管咋样,六指叫哨马孙子也不合适,就叫了一声哨马,眼睛里就有无限的期待,暗淡且无光泽的眼睛突然一亮,好像哨马就是突然降临在他面前的救世主一样。因为哨马手里握着扶贫款。哨马毕竟是哨马,如今村里大权在握,比不得一般人。给六指当孙子实在心无所愿。心想,叫你叫哨马,你就当真了?心里就有愠意。这可怜之人还真是最有可恨之处!半开玩笑说,你本骈母枝指,废物一个,活着费些粮食,死了臭块地,活着有啥用处?你就是死狗扶不上墙头,扶你也难扶哩。不过,还是假眉三道地叫了一声六指爷爷,也不破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俩人就在心里斗法。
六指听懂后半句,原本知道自己活着对社会也没啥用处,年轻时不学好,落得后半生可怜。不由晃脑袋问哨马,啥叫骈母枝指?哨马笑嘻嘻说,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六指把右手从棉絮里拉搭出来,拇指边一个软叽叽的指头耷拉着。哨马指着说,这就叫骈母枝指。六指笑笑说,你那话深奥哩!俺听着难懂!你还甭说哩!俺就凭这骈拇枝指好歹吃喝了多半辈子!懒人自有懒人的活法。哨马揭短说,是啊,你爷爷末了穷得连老腌菜缸都卖了。没的卖了,就叫你老婆捡着家里值钱的卖,卖了钱东西还在。可惜,你老婆也死了。六指嘻嘻几声,你说俺吃软饭?眼睛瞪得老圆,脖子伸得老长。
怕你提哪壶你就提哪壶?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六指最怕提起老祖宗们卖老腌菜缸的事情。早先年间,有些人家穷,叫外人给自家拉偏套,就像驾辕的牲口再用别的骡子拉梢一样,帮衬着就力量大,拉得也多,上坡就有劲。六指不怕揭老婆的短,世上人原本笑贫不笑娼,卖个那值钱的物件怕啥?好歹卖了钱东西还在,又不折本,那怕个啥?可每当人们提起他祖宗卖老腌菜缸的事,就像戳他心窝子一样难受。哨马心里的愧疚正是因此而起,因为买了六指祖宗老腌菜缸的不是别人,正是哨马的爷爷。
六指年轻时当然没少听父母谈及自家祖宗们当年那点破事,心里常常为这件事嫉恨哨马全家。哨马家铺的盖的,吃的用的,哪件不是花俺老贶家钱买的?六指年轻时常常跟村里一伙同伴大小,甚至和水塘边女人们也常常磨叽此事。如今哨马先人都已驾鹤西遊,就把这点旧账全算在哨马头上。冷不丁也把这老生常谈说给后生们听。哨马最烦的就是这一点。莫非你要把这点破事流传永辈子?如今上面叫把扶贫弄准确点,哨马头一个就想起六指来,这不是因为六指贫穷就帮扶他,而是源于心里那点抹不掉的纠结。这纠结由愧疚渐渐转化而成。哨马知道,六指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的懒惰而成,可他确实是村里最贫困的人员之一。哨马帮扶六指,不仅因为六指是村里最具贫穷的典型,做为一村之长,若是把六指帮扶起来,既能做出成绩让上面看看,也能借此机会补报六指一点什么。也好堵堵六指的贱嘴巴头子,并以此减轻对六指祖宗那点愧疚并消除因此对自己形成的社会压力。
哨马还没说起扶贫的事,就先说起老腌菜缸的事。六指就不愿意,反说哨马是老狗忘不掉千年屎,老把这事挂在口头闹毬哩?哨马知道自己又说漏嘴,就拍拍六指肩头,咱今后谁也不说了,你佬不说,俺不说,你不说,俺不说,谁也不知道。六指嗯一声问,今个来干啥?哨马转入正题,给你佬修房子!六指跳下地高兴地唠叨,俺这死狗也上墙头了?哨马说,你原本是死狗扶不上墙头的,可如今国家有政策,扶上扶不上,也叫你佬这死狗上墙头哩。六指也不哼哼了,那俺就趁乎着豁出老命来就上这墙头吧!哨马告诉六指,不仅给你佬修房子,还要给你佬办低保、申领救济款!不知哨马出于何种动机,又跟六指耳语,村里早就有人站出来反对,说老六指致贫是因为他懒!可俺哨马说,咱不问原因,只看现实!国家也没说哪个懒汉穷了,就不扶持他?六指就胡毬着答应,对着哩!
哨马心里所想和国家大势六指根本不知道,也压根儿不想知道。但他的眼睛时时刻刻和村里所有人一样,都眼巴巴盯着哨马手里的扶贫款。甭看六指半死不活的模样,心里明镜也似。哨马给谁谁家办了低保,给谁谁家翻盖了新房,他老六指都一清二楚,只是碍着老脸还没有直接到村委会去质问哨马,为啥给谁谁办了低保、救济金,翻盖了房屋,也不给俺弄弄?就凭你爷爷昧了俺祖宗八大缸老腌菜,也得给俺弄弄!六指没跟哨马直接说,谁叫咱是祖孙关系?可是经常到水塘边跟浣洗衣裳的女人们唠叨。
这话就传到哨马耳朵里,哨马为洗清自己,就跟旁人说,当年俺爷爷买六指祖宗老腌菜缸,也是两厢情愿的。俺爷爷也不知道他家祖宗把白花花的银子暗藏在老腌菜缸里!谁知道吃老腌菜还吃出银子来?后来俺祖宗见吃老腌菜吃出银子来,不知是福是祸,吓得双腿都打颤颤,银子花得也不坦然自在。六指听说后,你祖宗花白来的银子不坦然,俺祖宗丢了银子就自在了?俺经常还替俺祖宗后悔得肠子都断了哩!后悔也是白后悔哩!哨马得便宜卖乖乖说,也不知道他老贶家哪辈子损下阴德,就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送给外人了!
哨马话是这么说,毕竟替爷爷背负着对老贶家的一点愧疚。哨马原本想通过扶贫抹平六指心里的那点不平。可六指心里却老想着祖宗们当年那点破事,像数家珍那样跟哨马唠叨着老祖宗卖老腌菜缸的事情。六指愤愤说,那个趁火打劫买了俺六指爷爷老腌菜缸的人还不是你哨马的爷爷?六指唠叨个没完没了,唠叨得哨马耳根子发痒。六指听说给他修房子,还要给他办低保,申请救济款,一颗心跌在肚里。此时,哨马似乎像还了六指家老债一样,再不提起老腌菜缸的事了。六指得了便宜却又提起旧话来。
三十八年村里搞土改,俺爷爷虽然穷得没法过日子,也不至于把老腌菜缸都卖了哩!还不是你爷爷趁火打劫,说家里吃干饭没菜下咽,硬要买俺家老腌菜缸?再说也没听说过,哪家子哪辈子,谁家穷了,还把老腌菜缸都卖了?哨马说,那还不是你爷爷眼见得天下将要大变,怕挨斗争,贿赂村保地保,叫官牙子撮合,贱卖了几百亩土地和几处老宅?最后卖了老腌菜缸的?六指说,是啊,俺祖宗留下几亩山圪梁地也打不下几斗粮食,家里穷得没法子,就把八个缸老腌菜也卖给了你爷爷。说来道去,还是贶氏子孙不屑。买老腌菜缸的人并没有错误。
六指惋惜地说,谁知道老祖宗在老腌菜缸里暗藏了几千银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送人了。没那啥的可那啥了,那啥的可没那啥!六指想说,原本应该得到的却没得到,不应该得到的却得到了。只是这话说起来不好听,也不能直接说出口。六指说,这是造孽!哨马说,你佬绕来绕去,还是嫉恨俺?作孽也好,不作孽也罢,那都是老一辈子人们的事情了,也不应该记在俺头上。俺也没吃过你佬祖宗一个老腌菜疙瘩,也没花过你老祖宗一两银子,你佬紧管说这些老辈子事情干啥?
六指愤愤说,你这样说可是胡说八道哩!咋就说,你没花过俺家银子?没吃过俺家老腌菜疙瘩?甭看六指绕着口说,其实,六指就是想说,俺六指不管咋说,如今就是穷了,就是逼着你哨马给俺办低保、救济金,盖房子哩!六指突然说,若不是俺祖宗当年卖了老腌菜缸,如今俺还用不着你哨马上赶着到俺家门里扶贫哩!怕不是拿着俺家钱给俺扶贫哩!拿俺的拳头捣俺的眼窝子?其实六指就是怀疑哨马家里还藏着祖宗们没花完的老腌菜缸里的银子。
六指并没有胡说,当年哨马爷爷祖上三代像“雅各下埃及”那样从老州城逃荒到关南又从关南像“摩西出埃及”那样逃荒回到“流着奶和蜜”的丰腴村,领着一个邋遢女人和拖五带六的光屁股儿子,就住在六指家牲口棚里,租种六指家卖剩下的山圪梁子地,出门和老婆分穿一条裤子。但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确确实实是黄河的子孙,丰腴村没有“奶和蜜”,奶和蜜样的煤炭资源被当地黑把头和官府掌控着,后来就买下六指家八大缸老腌菜也舍不得吃,上面吃完就再添些芥菜疙瘩,一直吃到再次土改时分地主浮财,贫农团给他家分了几亩地和三间房一处院子,第二年秋后就收了几石谷子,除了交公粮和村里摊销,剩下的足够吃喝嚼裹了。住处也有,那八大缸老腌菜也不稀罕了,渐渐吃到缸底,露出白花花的银元。哨马爷爷看着白花花的银元,一下子吓坏了,若是被八路军知道,还不把咱家当地主斗争了!再给自己弄个私昧别人财物的罪名,那可是了得?
于是,就把银元全部弄出来,留下几块也怕露白,就把其余的拿几层子包袱包着、袋子兜着,埋在院里杏树底下。解放后一块一块偷着到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花,六零年别人家饿死了人,哨马一家子可过得舒舒服服。花不完的银元,哨马爷爷就悄悄藏起来,谁也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临死那年,把藏银地点悄悄告诉给哨马,就连拉五拉六的几个儿子和另外十几个孙子也都被蒙在鼓里。动荡那年,不知村里哪个多嘴的婆婆,把这事抖搂出来,哨马爹因此还戴上阶级异己分子帽子,被群众斗争了不知多少回。六指家因祖宗早早把家产挥霍了,穷得叮当响,划定成分时被弄成贫农。哨马到手的银子也成了死宝。
如今,六指住着透风漏雨的几百年的老房子,比哨马他爷爷当年逃荒到丰腴村时好不了多少。因此,被哨马列为丰腴村首个贫困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六指旧事重提,哨马心里虽然愧疚,也不愿意,就跟六指说,虽然事实如此,你也不能说,提起新的是新的,拿起旧的还是新的?没完没了说个不停,俺给你办低保、申请救济金、修房子还不成?你唠叨个毬?六指呛他,不是俺先说起的,是你哨马先提起的。俺又没卖老腌菜缸,还管毬那祖宗的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