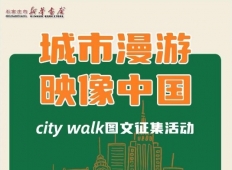张京华《燕赵文化》第八章:北方民族大融合
唐代的安史之乱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又一次大变动。在安史之乱发生的数年间,“天子去蜀,多士南奔”,“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新、旧《唐书》记载当时人口流失的情况说:“东周之地,久陷贼中,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今河南武陟),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关中北至河曲,人户无几。”
所说北方人口的流失变动,也包括河北在内。如《全唐文·博陵崔府君神道碑》就记载了博陵大族崔氏在安史之乱发生时举族南迁一事,说:“天宝时末,盗起燕蓟,公超然脱屣,遂以族行,东游江淮。”不过,唐代这一次人口变动主要限于战乱发生的数年之间,其规模自应比两晋南北朝时期要小。有人引李白的话说安史之乱中“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认为这一次人口迁移可以与“永嘉丧乱”、“靖康之难”相比,但是李白所说往往言过其辞,不足以作为史实的依据。并且安史之乱中受破坏最大的主要是在洛阳、陕州、函谷、关中一线,河北地区的人口变动是有限的。在安史之乱及此后长期的藩镇割据中,河北地区的人口不可能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但也不至下降到洛阳、关中的水准。比较充足的农业人口以及兵源,正是河北藩镇得以持久延续的重要基础。
除了一定限度的人口数量的变动外,在河北地区出现的“胡化”现象中也包含了血缘融合的因素。当时河北之地的“胡化”,是将汉地农耕文化与胡族部落血缘军事制度兼容并包,并上承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的尚武传统,但其中也不无血缘的融合。安史之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等就多为胡人,安禄山为“羯胡”或“柘胡”,羯胡就是昭武九姓胡,本月氏人,以曾居祁连北昭武城故名。唐史中又称昭武九姓胡与突厥族的混血为“杂种胡”,安禄山父是昭武胡人,母是突厥人,故又被称为杂种胡人。史思明也是杂种胡人,其余各游牧部落胡人如契丹、奚、高丽、渤海等还有不少。安禄山用来作战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卒)和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到史朝义兵败逃回范阳时,随从的胡骑只剩下数百人,其余大部分如果不是战死,就是留在各州郡中了。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有胡人子胤又从而萌发胡心,说明胡化程度已很深入。此一点,河北之地较之人物荟萃的长安,应不相上下。所以唐史中称:“彼幽州者,近染禄山、思明之风,”“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陈寅恪称河北之地是“胡化深而汉化浅”。
宋元明清时期,契丹从黄河以北等地强迫迁往关外契丹故地的汉族人口有一百万人左右。辽国人口总数为三百三十万,汉族人口为二百四十万,占辽国人口总数十分之六以上。女真族的情况也是一样,本族人口稀少,地域数千里,人口仅十余万,有金一代强迫迁徙出关的汉族人口有数十万人。在关内方面,女真人进入中原以后,仅在河北、山东、关西安置的屯田军户就有一百三十余千户(每一千户为三百人),总计迁入的屯田军户有一百多万人。女真人喜欢穿“绛色紫衣”,引起杭州一带也盛行胡服,称之为“番紫”。女真人还强制汉人剃发易服,从其习俗,“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发式是古代汉族的又一重要特征,汉族居民改变发式即由此时开始。元代把全国人口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色目人是对蒙古族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及欧洲各族人的统称。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列举色目人有三十一种之多,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中列有二十三种。蒙古族内迁以后,众多的色目人也相随留居内地,明人邱濬《区外畿甸降夷》文中说到明代初期,“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在“汉人”中也有八种名目,契丹、女真、高丽等都算做“汉人”,狭义的汉族人则称为“南人”。契丹等“汉人”的血缘融合自然更不会后于色目人。清初满族人举族入关时,人口总数约为九十到一百万人,其中除满族八旗外,还包括一部分与之相邻的东北北部土著民族,如黑龙江索伦各部、奴尔干人、古鞑靼人、“鱼皮鞑靼”(即赫哲族)等。延续至近现代以来,满族人与汉族人的融合同化最为完全。
大体说来,在每一次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地农耕民族的战争冲突之后,汉族地区特别是河北地区,都要经历一次汉族人口相对减少、北方民族人口相对增多的过程,战争平定以后,再逐渐地增殖。每一次反复之后,都有更多的北方民族血缘融合进来。不出数十百年,移居汉地的北方人口一旦更易姓名,就很难再加区别,积习一久,两相忘怀。只有个别地方,经过专门的社会调查之后,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发现。如经过社会调查和文献印证,可知现在居住在山东章丘的术姓(术虎氏)、傌姓,河南固始县的祝姓(竹负之后),洛阳孟津、新安、渑池等县的李姓(木华黎之后),平顶山的马姓、宣姓,镇平、内乡、淅川、新野、南召、南阳六县的王姓,福建惠安的出姓,南安的黄姓,都是元代蒙古人或者是色目人的后裔。像这种情况,如果说其中的一些希姓还会引起人们偶尔的注意,那么其中的李姓、王姓,粗略一看,恐怕谁都会以为它们是汉族大姓。又如清嘉庆年间,留居云南的蒙古人与丽江纳西族人融合后,以“和”为姓,时间久了,自己也以纳西族人自居。后来通过其祖坟的塔形蒙古文墓碑的印证,才得知其祖籍原系蒙古,于是将姓氏从“和”改为“元”。像这种尚能得到某种印证的情况,在上古以来的民族融合中自然百不余一,绝大部分民族融合的痕迹都已不复可寻。登台怀古,而物去人非,不仅炎黄之迹不复可识,北朝豪强士族之迹不复可识,就是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也都不复得知了。
|
- 05-05国际舞英荟萃 点燃观众热情
- 05-02承德市创建首个诚信示范园区
- 05-01全民阅读 耕读传家 书香中国
- 05-01尚善友爱济困“致敬英雄 关
- 04-30筑广厦 济苍生 青春联谊 共
- 04-27健康中国行|燕赵名家走进美
- 04-25【铁色之旅】春风渡我归流年
- 04-25永定河流域官厅水文化研学基
- 04-24传承创新发展非遗传承人胡凌
- 04-23防灾预警理念先行访发明家高
- 04-23刘剑新:“回望,是为了更好
- 04-22明湖画韵 情系老兵 摄影纪实
- 04-20为百姓分忧解难“春雨工程”
- 04-18无限诗情乘青少一颗赤心系家
- 04-184.23世界读书日:石家庄市新
- 03-24阳春三月
- 12-23杨华诗歌十首
- 12-21变了,我的家乡
- 12-18手机摄影:冬雪八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