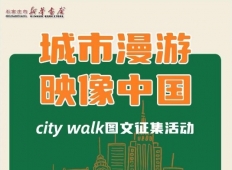评论:承德“地标性”现代诗写与 诗人的文化使命
摘要: 避暑山庄自建园之初,就已决定了它在一个城市崛起和兴盛的发展过程中的地标性建筑的历史地位,如同黄鹤楼、岳阳楼、华清宫等,成为一座城市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名片。其所唤起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余秋雨语),不仅仅是 ...
避暑山庄自建园之初,就已决定了它在一个城市崛起和兴盛的发展过程中的地标性建筑的历史地位,如同黄鹤楼、岳阳楼、华清宫等,成为一座城市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名片。其所唤起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余秋雨语),不仅仅是清代第二政治中心的皇家记忆,还是一种园林风景微缩文化的典范,一种帝王诗写的景观文化记忆,蕴含着深厚的地域文化的绵久力量,脉脉沉淀、流淌在现代进程中的承德文化血脉之中。 但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历史与现实的渐行渐远,甚至地标性建筑某些景观的毁坏与破损、修复与重建,很多只能是教科书级别的知识记忆,或文化名流得以流传的题咏诗赋所建构的文学景观,而后者似乎更具现代人的共鸣与共情。因此,一个城市的地标性文学景观,都是在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心灵发现和文化体认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记忆体系,对山庄文学景观而言,也有着一代代帝王、扈从文臣、文化名流、民间文化记录者们辛勤的文本化耕耘,从而掀起两次书写高潮,一次是在康乾盛世,康乾帝王所呈现的热河诗歌,特别是避暑山庄七十二景的景观诗歌,跳出清初诗坛主流“神韵说”而独创机杼形成“以命意为上”的诗学理论,使诗歌思想超越诗歌技巧的实践创作成为可贵的文本借鉴和心灵图景。一次是20世纪 80年代“山庄文学”的兴盛,以及“承德作家群”的崛起,各种体裁创作异彩纷呈,优秀作家阵容庞大,以其浓郁的塞北文化气息,提炼着承德边塞开拓精神与多民族和合气象。 然而,写山庄的诗歌固然很多,但大多散碎、随性,缺乏系统性观照,更难于触及康乾七十二景的高峰写作。显然山庄“地标性”现代诗写还有着太多空白和遗憾。当静默的七十二景在去岁冬日的某一个清晨,突然在一位叫王琦的诗人的心灵图景中一一盘活,透过短小精悍的七十二景现代新诗写作,一个王朝鲜活的历史重新被浓缩在诗意之中。 王琦先生的七十二景现代诗写,正是当代诗人沿着历史的足迹走进皇家园林的一部心灵契合之作。它的诞生,创造了“山庄文学”的第三次高峰,填补了承德“地标性”现代诗写的一个遗憾,一个空白,激活了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文脉的诗意传承,自觉践行了一位新时代基层文化工作者、文联领导者、诗歌领军者的文化使命。 一、从历史到现实的形象力 王琦是位学习型诗人,更是一位有趣的诗人,他不仅通览古今中外诗歌,他更喜欢看杂书,他谦逊地说,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广泛阅读是他弥补知识的渠道,但他也风趣地说,他的阅读让他有了庖丁解牛的游刃之感,更能从中窥见一个宇宙,他让他自己在那里燃烧。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王琦的善学善思,成就了他的优秀品质。也成就了王琦的诗歌成长之路,从20 世纪 80 年代的诗歌写作,90 年代的停笔沉思,再到新世纪之初的触网归来,以及最近十年的从容崛起,进而抵达了诗歌写作的高峰,不仅跻身于全国各大文学官方刊物和排行榜、优秀作品集,更是连续获得河北省十佳诗人奖、孙犁诗歌奖、《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他的诗集《灵魂去处》《王琦诗选》《马在暗处长嘶》,以其显著的现代品格、苍郁的哲思调性、举重若轻的诗意表达,让他成为一位辨识特征极为鲜明的诗人。 其来有自,王琦的诗意始终扎根在他生活的热土之上,承德,既完成了他的城市诗写,也建构了他的乡村表达。然而,他更多是匍匐在生命气象的辽阔之中,那一声声从灵魂深处长鸣的马嘶,缭绕在避暑山庄丽正门旁的下马碑前。或许他阅读时的那种游刃之感,让他获得了自由出入的从容。王琦曾写过两首同题《诗人》,收入在诗集《王琦诗选》中:一首有名句“复活的诗人!心仪天下”,原来这种“心仪天下”的敞开,一直令诗人在不断拉近三百年山庄的历史,让康乾盛世中的皇家园林,帝王题写的七十二景,都在“明君”志向的主体情志中获得共鸣:“我站在当年康熙站立的地方/感受着他的雄才大略/似乎听见了历史的回声”(《澄波叠翠》);一首有“真正的诗人坐在黑夜之中,/四周全是鸦雀无声的文字”,这种“坐忘”的宅寂之感,一直令诗人成为他自己,一个干净透明的人:“我们的视线不在一个视点上/却都想到了远古时代/那种高山流水般的自然与澄明”(《静好堂》)。于是,在灵魂的淘沥与淬炼之后,自省与自觉之后,王琦的山庄诗写应运而生,时而呈帝王之思,时而抒自我之怀,悠游余裕,又意味深长。“景行行止”,这部新诗集的题名也便恰如其分地呈现了历史文化的明澈和现实意义的通达。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说:“一部艺术品只是对那些掌握了文化能力(亦即可以译解符码能力)的人来说,才会是有意义的和有趣的。”无疑,王琦具有这项能力,他发现了山庄七十二诗意景观的无穷魅力和独特价值,他在游览诗意景观与鉴赏帝王诗写、感受康乾二帝时,在俯仰之间有了一个相互确证的循环过程:一方面,七十二诗意景观印证了王琦对康乾诗歌和帝王的想象,加深了王琦诗意创作的形象化;另一方面,经典的诗歌、空留背影的帝王和现实中生动的七十二诗意景观,又激发了王琦在观看的盎然兴味中,重新创造属于当代人自己的诗情建构和诗意表达,使诗歌创作获得了形象力。 善学善思的诗人王琦,从中国现代诗歌中深切领悟到形象化和形象力的有益元素,吸收融化,双向并举,既注重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历史与现实,又追求形象在诗歌中的表现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力和感染力。比如首篇《烟波致爽》: 在这个大殿前足足坐了一个下午 我要体验一下虚无缥缈是什么状态 脚踏实地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顺着当年康熙或者乾隆的目光 扫一眼东西跨院 这里曾经是帝国的中枢 深夜里的一声咳嗽 上千平方公里的河山都会惊醒 如今,一把锁锁住了满园春色 只留下史书里的冰冷 西暖阁里,两位皇帝先后离世 帝国的大厦将倾未倒 却也风雨飘摇 最深刻的是辛酉政变 一个颇有争议的女人 在这方寸之地,打乱了一统江山 《北京条约》《瓊挥条约》 无不与这间大殿有关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 一间卧室,让中华民族 昏昏欲睡了百年 再美的景色,也需要有欣赏的观众 轮回交替之中 当年的帝王将相 都已化作尘土 ----《烟波致爽》 “烟波致爽”作为康熙三十六景第一景,“帝王寝官”的官殿形象栩栩如生,大殿,东西跨院,西暖阁,甚至辛西政变,丧权辱国的条约等,将一座帝王寝官的布局和故事,立于翔实可感之中,苍茫的历史风云,在典型的历史情绪中燃烧起来,升起一缕缕精神的冲击。这是形象化的魅力,同时也因为“我”与康熙的神会又独立,让这所康熙的实际存在物的宫殿形象,从而具有了精神现象,有时是和烟波致爽统一地表现出来,“如今,一把锁锁住了满园春色/只留下史书里的冰冷”“一座山庄半部清史/一间卧室,让中华民族/昏昏欲睡了百年”,有时又是从诗人“我”的胸臆之中直接抒发了出来,“在这个大殿前足足坐了一个下午/我要体验一下虚无缥缈是什么状态/脚踏实地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再美的景色,也需要有欣赏的观众”,但光有浓情的程度还不够,还需要达到思想的力度:“轮回交替之中/当年的帝王将相/都已化作尘土”。这短短的三句诗行,实在是考验了王琦的功力以臻至境,已切实蕴含了文化思想的,乃至美学的力量。 在本诗集中,这样可感的形象化,进而化为形象力的表达比比皆是:“两座拱桥,连接三条飘带/一个微风和煦的下午/一只蚱蜢舟/让这幅水彩画动了起来/估计当年康熙、乾隆都没有想到/沿着自己当年的御路/每一位游人都可以/走进自己的深宫”(《芝径云堤》)、“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院落/所有的摆设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让人唏嘘不已”(《水芳岩秀》)、这是“康熙三十六景最后一景/但是故事到此远没有结束/那些花团锦簇的下面/有多少往事,像这人去楼空的亭子/让我们深思和凭吊”(《水流云在》)、“大厦将倾的时候,青砖是无辜的/能够看见的坍塌可以挽回/看不见的/在地基以下/皇帝与宰相都无法听见青砖的呻吟”《勤政殿》)、“大船往湖的深处去了/二百多年过去/码头都重修了两回/我依然觉得此情此景/比梦还轻,像一片鸿雁的羽毛/漂在水面上”(《青雀舫》)。 尽管在七月诗派的理论建树中,形象化和形象力有着严格意义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诗学探索,两者并未共生并存,恰是各有取舍,而在王琦的诗歌创造中,他总是能够以融合之姿、化合之态,将承德“和合气象”发扬光大,烛照诗意与人生,自信地收获着品相独一的诗歌创作风貌,既赋形于承德山水园林感性形象的眼睛爱抚般的坚守,又在灵魂的交通中内蕴着举重若轻的感人力量: 其实历史和现实 就如同迈过这座桥这么简单 看似不经意,都是一首诗 —《水心榭》 二、从地理到心理的身份感 王琦的早期诗歌,并未取得身份的自觉,更多是在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文化思潮冲击下,在文本中应时代召唤而呈现出知识分子矛盾性的双重探索,一方面是冲破思想禁锢的时代精英意识,一方面又呈现出面对一个敏感时代的内在的迷茫和冲撞,《灵魂去处》中“在斜插过旗帜的地方/站立着一个沉思的人”(《身临其境》),“但目光就是路啊/抬不起头来/无路可走”(《目光如路》),这里有着对国家、社会、人生的直接追问,也获得了“有心无心之悟”。但自新世纪之初,开始触网归来之时,尤其是《马在暗处长嘶》诗集创作的时期,尽管还仍然一以贯之有着内在的悲情和忧伤,但已经在日渐自觉并立体化的个性自我中得到疏解,那个时代感召下的知识青年的青涩形象从抒情主体中偏移,那个举重若轻、洞悉世事的容智的王琦,有了抒情主体形象的自觉且渐趋成熟的确认:“远处的大雪漫天飞舞/雪地上一个沉思的人,默默地/面对着旷野”(《寒梅》)。“一个沉思的人”,是王琦真正作为诗人的身份,他从“斜插过旗帜的地方”到“远处的大雪漫天飞舞”,历经了青年到中年的蜕变,但不变且更为自信的是作为“沉思的人”的独立的诗人身份。他的诗人自我,不再是被动和隐含起来,甚至也不需要再借助清醒的对抗:“绳索也涨价了,一个想上吊的家伙自言自语·……”(《灵魂去处·那些年》)来隐藏,或借助无奈的排距:“迟迟写到最后/如果还是动词与形容词的相拥/那么,我宁可不再完成”(《王琦诗选·一首诗》)来退隐,他终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让我想起你,我的王子/一匹白马,正浪迹天涯”(《马在暗处长嘶·我读懂了一场雪》)。从心开始,随心而安的诗歌王子,这是王琦给自己最好最恰当的身份命名。 而今,《景行行止——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意》的写作,更鉴照了王琦如同诗人多多一样,“保持诗人身份的唯一性和纯洁性,将自我完全寓于诗歌之中”。这或许可以看作,他献给自己即将步入退休生活的一份厚礼。在这本诗集中,王琦更为纯粹和透明,他一边固守着作为“浪迹天涯”归来的诗歌赤子的自由和沉思,一边在承德历史这一血脉相连的文化联系中发现诗歌新的可能性,并让一个诗人的身份,在“避暑山庄”这一特定历史文化场域中,既有意象的呈现,又有文化的定位。诚如德成师兄在《序·胜景之下,诗意栖居的菩提》中所道出的:“王琦的诗歌,拨开看似粗线条的表象,你会发现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灵动内核在成熟中跌落。他正用诗情的命格,完成个人主体意义上的救赎,以期对得起这片生于斯养于斯的‘洞天福地’”。 “我”作为抒情主人公,诗人的主体身份最为饱满。“我”的立场并不做廉价的抒情,而是巧用活用小说手法,让“我”成为一位叙事、造境的高手,很多题景诗,都是一篇小小说,或者是一幕情景演出,充满了鲜活的历史细节和画眼睛、勾灵魂的笔墨趣味。比如王琦在题写康熙大帝的《梨花伴月》和《长虹饮练》,乾隆皇帝的《颐志堂》和《凌太虚》时,都是在“我”的讲述中徐徐穿越时空,缓缓打开一幕幕帝王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的康乾二帝,有“漫天的月色/一树树梨花”美境中妃嫔赏月的惬意,亦有“一条彩练舞在空中/如同巨龙俯身饮水”“佛祖端坐在莲花瓣上”幻境中心执莲灯的顿悟,有“这是他与爷爷一脉相承的地方/喜欢在颐志堂中博览群书/找寻治国之策”视镜中祖孙相携之乐,亦有“人间与仙境/以此亭为界/进是太虚之境,退是人间烟火”心境中登高望远的释然,其中“我”只是一个叙述者、见证者,从容余裕地把诗歌的抒情特质,转化成一种透明体,干净,内敛,又不失点头颔首的会意,不言自明,不喻自清,“一定有诗人主体身份意识在诗歌中的呈现,除“我”之外,还聚焦在康乾二帝的“君王”意象上。传统诗学中的“意象”,带着日常丰富鲜活的图景却又具有得意忘言的共情特征,王琦颇具现代情怀的诗歌之“王”,让他能够在进入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写的时期,完全自主而有意识地完成了君王的民间化,赋予一个历史上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承担着普通人的生命感知:“坐在湖边/眯着眼睛,在自我陶醉中/像一位民间老人/忘了自己的天子之身”(《无暑清凉》)、“此时的康熙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许慈爱/像一个跨世纪的老人”(《甫田丛樾》)、“它们曾经围住过一盘炉火,一个老人/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朝廷”(《勤政殿》)。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中,有着解不开的“老人”情结。老庄乃儒道至圣,村叟、田父、渔翁、樵夫都是中国诗词绘画入境的老人,“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更是独属老人的境界,老人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隐喻和象征。于已逝的历史而言,盛世帝王与老人皆有着人生了悟者的智慧和传统文化的启示性。显然,王琦有着天生诗人的敏感又敏锐的特质,他知道,有时候君王的心路历程是需要大胆假设的,在这些诗作里,王琦有时候就是康熙,有时候又是乾隆,仿佛康熙和乾隆也有着相同的身份置换,有时是君王,有时是诗人,他们视为知己,互为同类,在与自我的对话中心怀天下,贤明通达,又任心随性,平凡普通:“站在这群山之上,脚踩四面祥云/凡夫俗子/也会有一览众山小的胸怀/何况一国之君”(《四面云山》),“马背上,仅仅一墙之隔/一边是想象,一边是现实/有时君臣之间,又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丽正门》)。他们同呼吸,共悲欣,感同身受:“无一例外/必定来这里驻足一会儿/只为能看到冰雪之中的偶像”(《南山积雪》),“随口品评:逸少哇逸少/你如果看到这一景观,是否会觉得/曾经的往事不过是虚名?”(《曲水荷香》),“而他自己/如同一位世外高人,沿着/一条梦中的小路,转身离开”(《采菱渡》),“只有这两千多年的距离/让我忽悠一下/从皇帝的梦里又变回到平民百姓”(《清晖亭》)。在历史的名胜古迹前,王琦有时候既是灵魂的探险者,也是一位清醒理性的研学者,在与他者的讲述中点化命运,让时间做出应有的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 斗转星移,三百多年过去了 这里只剩下当年的地基 但是作为一国之君 他那严谨清醒的头脑 即使放到现在,也有现实意义 —《西岭晨霞》 这些皇帝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辛苦 他们也是人,不是神 走下那把龙椅,也和蔼可亲 甚至值得尊敬 ---《万壑松风》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是抒发诗人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所以,一首好诗,或明或暗,“我”必在其中,王琦诗中抒情主体的身份意识,让抒情有了更为丰富、鲜活、真切的效果,令人在一呼一吸间感受着满腔深情,于一园,于一城。 三、从名胜到生态的文化观 王琦作为一个成熟型的诗人,他早在2010年的一次网络研讨采访中,明确指出:“我预测诗歌会朝着关心民间疾苦,关注社会变革等核心价值领域发展,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诗歌定然会为读者和时代所抛弃。”无疑,《景行行止》的创作成为一个明证,他在城市的漫游中出入历史与现实,并有意识地承担起一个人、一座城的文化使命。 我顺着当年的御道拾级而上 到达山顶 已气喘吁吁 在康熙、乾隆都曾远眺的地方 看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拔地而起 看到了历史的进步、岁月的层次 -----《四面云山》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在强调历史的“现代性”,强调某种精神上链接的重要性,强调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王琦作为诗人,承德市文联主席,有着非常强的文化使命感。避暑山庄作为伴随他成长的历史遗迹,他是有着游客和主人翁的双重身份的,他对山水景观、七十二名胜的自然风光并非只是流连欣赏,他在陶冶性情的同时,还非常珍视那些丰富的文化胜景,以及内化于这些文化胜景中的历史人物和精神内涵,表现出了以诗记录与保护、文化开发与活态传承的自觉意识。诚如他内心淙淙流淌的“风泉清听”,亦有着知音、知己之情:“香案仍在/人去楼空/失去了根基的往事/还有谁/能像钟子期一样/听出这弦外之音”。(《风泉清听》)因这“弦外之音”“我猜想作为皇帝的他们/一定能够感受到苍天之下/顶天立地的使命”(《万壑松风》)——“顶天立地的使命”,从而成就了他的短小精悍的现代新七十二景诗,并以此涵盖了一个王朝的历史,同时也鉴照着一个现代城市发展的新风采。 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善于沉思的王琦还看到了什么? 他在《石矶观鱼》看到了康熙:“他经常教育自己的皇子皇孙/要顺应自然/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他也在顺应‘道’”(《石矶观鱼》),在《观莲所》看到了乾隆:“他肯定想到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应该顺应天道,都应该在沉思中/冷静地思考和观察”(《观莲所》),王琦看到的是历史的必然,指出了顺势而为是每个朝代都必须顺应的;“康熙深知要恩泽百姓/天下太平/才能成为有道明君”(《延薰山馆》)、“铁打的江山,民为根本/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才能天下太平,才能顺应天意”(《乐成阁》),王琦看到了康乾身上勤政爱民的仁君志向、民本思想和德治天下的成功举措,“移花接木的本事成就了避暑山庄/天下一家的思想成就了康乾盛世”(《濠濮间想》),王琦是在诗意地提炼中萃取着滋养仁心的精神营养;在盎然的诗情中,当“也可以说,康熙为他母亲/在大花园中建了这座小花园”(《松鹤清越》),当乾隆“抚摸着一棵棵树干/就像抚摸着爷爷的躯体”(《嘉树轩》),并将自己所题的36景诗名都少于康熙的4字题名,王琦看到了身体力行的孝子情怀,正在“暗香浮动”;“在山水之间/找到返老还童般的一条小路”(《无暑清凉》),“在山水之间/找出一些细微的差别”(《镜水云岑》),“他以这种方式修身养性/把身心融入山水之中”(《永恬居》),王琦看到了乐山乐水的雅致情操,不仅蕴藉着深沉的宇宙观和自然观,更唯美地传承了生态文化的精髓。 这些“历史的回声”,让这本诗集就像一个人站在语言的大海、思想的大海、审美的大海,时而涌动的热浪扑面而来,时而静水深流处明心见性,时而恣肆磅礴中高歌踏浪,时而温婉含羞时凝眸静观:“这些滴水穿石的声响/由远及近,远近交替/正是历史的回响”(《远近泉声》)、“我站在当年康熙站立的地方/感受着他的雄才大略/似乎听见了历史的回声”(《澄波叠翠》)、“向木兰围场,向一匹宝马的归宿/疾驰而去,马蹄阵阵/身后是一片历史的回声”(《试马棣》)。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写不尽的酸甜苦辣,人间冷暖与帝王成败,都在一念之间。或许“历史的回声”正告诉我们,在文明生态建设中要注重对传统文化进行多种形式和样态的传承保护,不仅会在无形中影响提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精神面貌,而且还会让这座城市展现出独有的人文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琦的《景行行止——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意》正是一座有生命活力的承德地标,它像一组组解码,为承德旅游做了一件有益之事,让避暑山庄诗意山水的宝藏訇然洞开,为承德的游客开启一扇胜境大门,从这扇门可以走进一个康乾盛世,走进一个不为人知的诗的世界。 作者简介:薛梅,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承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承德市作协副主席,民进承德市委副主委。 |
最新文章
- 05-09真服务服务真凝心聚力再启航
- 05-08龙腾盛世 舞动夕阳 舞蹈展演
- 05-08传古维新 巨作奇葩 访“神州
- 05-05国际舞英荟萃 点燃观众热情
- 05-02承德市创建首个诚信示范园区
- 05-01全民阅读 耕读传家 书香中国
- 05-01尚善友爱济困“致敬英雄 关
- 04-30筑广厦 济苍生 青春联谊 共
- 04-27健康中国行|燕赵名家走进美
- 04-25【铁色之旅】春风渡我归流年
- 04-25永定河流域官厅水文化研学基
- 04-24传承创新发展非遗传承人胡凌
- 04-23防灾预警理念先行访发明家高
- 04-23刘剑新:“回望,是为了更好
- 04-22明湖画韵 情系老兵 摄影纪实
最新图片
最新帖子
- 03-24阳春三月
- 12-23杨华诗歌十首
- 12-21变了,我的家乡
- 12-18手机摄影:冬雪八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