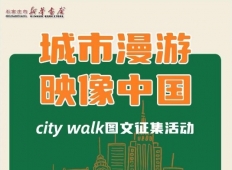颖川:朝华九章
朝华九章
1
有一天,我独自跑到三叔家去玩儿,突然问奶奶,“爷爷哪儿去了?”“走咧。”奶奶闪烁其词。三婶和岳嫂子也在场,然而都没释义。我不知道“走咧”是什么意思。莫非爷爷去了有金銮殿的京城,还是天津卫、保定府?我的猜测,并非没有缘由。记得娘说,爷爷是乡间有名的郎中,医治毒疮的妙手。京津保的官宦,有的还坐小轿车就诊哩。奶奶说的“走咧”,或许去了那些城市罢?
2
爹早年毕业于师范学堂,却不曾应聘去教书。我刚会走,爹便离开家门,做了高阳大姨家开设的染坊的掌柜,成年累月跟算盘子儿账簿子打交道。我天天渴望着爹来探家。一来亲亲我抱抱我,二来赏我一包绿豆糕或者江米条。平日,我连高粱糁枣饼子都吃得津津有味,而况西果子?不过,爹也不是每次探家都能满足我这个出了名的小馋猫;要知道,一家老少,全指望爹的那点薪水呐。
3
娘幼年不曾进学堂念书。她老人家的精通文墨,受教于家塾。姥爷和大舅是娘的启蒙老师。爹和娘是我的启蒙老师。我还不到两周,娘便从陈旧的箱子内,取出珍藏多年的清代启蒙读本,教我念“人手足刀尺”,念“山水田”,念“狗牛羊”。那篇读起来朗朗上口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极大地感染了我的稚嫩的心旌。我呀,依稀见到了江南的花草树木,乱飞的群莺剪影。我的耳畔,隐隐约约地传来鸟儿的歌声,莺儿的和鸣。
4
人们叫我小假闺女。乍听到这个外号,心里不是滋味;然而,仔细一想,不能怪罪人家。自己的某些行为,的确像女孩子。比如说,一个脑瓜顶上留着一块“小铲子”的小小子,偏爱坐在炕头上,跟着娘学纳割绒,学绣花。我给老姨用丝线刺绣的用以梳头的油拍儿,那艳丽的鸳鸯卧莲,活了似的。老姨说,这在群小中,找不到第二个。
5
我的爱好,也包括戏曲。这末说罢,只要听到附近村庄唱大戏的消息,不论梆子、老调、丝弦、哈哈腔,我都缠着爹娘领我去看;每场不吹喽“呜嘟嘟”,不离开戏棚子。这样,渐渐在我的心灵宇宙,萌发了同龄儿童罕见的戏曲意识。
6
那当儿,别看我小不点儿,也特喜爱花卉。阳春三月,我常跑到张家大院,欣赏盛开的一丛丛缀满枝头的璎珞般的白丁香和紫丁香;炎炎夏日,我常跑到荷塘,欣赏一朵朵或粉或白的大莲花,绿绒般的滚动着晶亮晶亮的水珠子的伞状的荷叶;八月中秋,我常跑到四叔(二爷的次子,大排行老四)家,欣赏释放清芬的玉簪和秋海棠。四叔是父辈中有名的吝啬鬼,莫说摘给我一枚大甜石榴,我想要一个喷儿香的白棒棒(玉簪的花蕾)都不成。
7
我六岁入学,先在离家较远的黎家学堂念书。一天上午,衣兜里装着一只知了,进了教室。青年教员刘鹏乐(论辈份,他该称我小叔),正给我们授课时,我的兜里那只不知趣的家伙,居然引吭唱起了蝉歌,哄堂大笑。鹏乐立刻沉下脸子,责令我把知了交出来,他即顺手当场摔死。放学后,我跑到他家,向他老娘告状;并且,非让人家赔我一只也爱叫唤的知了不可。当我回到家中,向娘诉说原委。娘不但不同情,还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8
一天下午,儿童团部派遣我和小雨,去把守北街路口,既盘查来人,又不许闲杂人暂时出村。我俩小跑溜丢,赶赴北街路口,门神似的,分立两旁。不大一会儿,从街里走近一位老太婆,手腕儿㧟着一个半成新的竹篮子,要到菜园里去揪马齿菜。小雨用红缨枪予以阻挡,不肯放行。我仔细巴睃,认识认识。跟小雨说,“这是老×,放她过去罢!”
9
儿童团部派遣我和小雨,除了那次到北街路口去站岗,还有一次上村西奶奶山去放哨。虽说都担几分风险,总归没离家门。但要出村,娘就不放心了,我还是个不满七岁的孩子呀。有一次,区里要在大杨庄检阅儿童团和青抗先。那里虽说离古灵山日伪炮楼较远,离我们村也不太近,我偏偏要去。
2017年12月11日,颖川记于燕斋。
【作者简介】
颖川 河北蠡县人。本名刘维燕,曾用笔名吴雁之、一丁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业作家。曾任南京中山文学院客座教授、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文学评委。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荷花赋》《羽片集》《临窗集》《我认识的文学家》、文论选《散文夜谭》、传记文学《阿樱传》、长篇文艺随笔《写人笔记》、系列散文《与燕子的对话》。现居河北涿州。
|
- 04-25【铁色之旅】春风渡我归流年
- 04-25永定河流域官厅水文化研学基
- 04-24传承创新发展非遗传承人胡凌
- 04-23防灾预警理念先行访发明家高
- 04-23刘剑新:“回望,是为了更好
- 04-22明湖画韵 情系老兵 摄影纪实
- 04-20为百姓分忧解难“春雨工程”
- 04-18无限诗情乘青少一颗赤心系家
- 04-184.23世界读书日:石家庄市新
- 04-17烈士碧血洒挂云英名长在祭拜
- 04-10河北省冀南商会召开联席会促
- 04-09第九届中国国际绿色能源与节
- 04-07畅享田园新生活第三届桃花旅
- 04-05河北省优化营商领导小组办公
- 04-04祭英烈主题诗歌朗诵会在解放
- 03-24阳春三月
- 12-23杨华诗歌十首
- 12-21变了,我的家乡
- 12-18手机摄影:冬雪八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