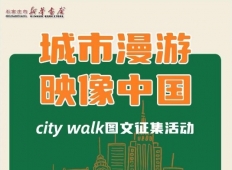绿窗:青纱帐哀歌——诗人郭小川的心灵风景
摘要: 1976年10月18日,他在异乡的床上,不曾一言,只把深邃的空旷,一个大寂静,投给错愕的世界。——谨以此文献给故乡,凤山古镇走出的诗人郭小川。
1976年10月18日,他在异乡的床上,不曾一言,只把深邃的空旷,一个大寂静,投给错愕的世界。——谨以此文献给故乡,凤山古镇走出的诗人郭小川。( 绿窗) 吴冠中绘 《甘蔗林与青纱帐》插画 1. 那注定是个凄凉至极的夜晚,一个经受了十年荒冷千般蹂躏的灵魂,被死神粗暴地带走,而没有一个人见证,哪怕听到一声嘶喊,或早于死神闻到无常的味道,秘密的恐怖的吞噬穿肠而过,一寸肌肤一寸灰,逼迫着灵魂起身。十指撒开,他终把自己当成残月升上了天空,像一场出乎意料的暴雨下到了地面,铁骑突出刀枪鸣。 而后是低徊持续的叩问。大地苍黄,死生契阔,显然,只有北方浩瀚的青纱帐才担得起这沉重的悲欢。世间再听不到,说出“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赘”那个豪迈的声音,再找不到穿越《青纱帐与甘蔗林》的诗人,伫立苍穹之下《望星空》的郭小川了。上帝和鬼魅同时来抢夺他,一个甩出蟒蛇的绳索,一个派来狙击的火神,梦想的拳头膨胀沸腾变幻,无助的呐喊,但终于没能冲开篱笼,留个焦黑的人形凹痕给世间。拉奥孔式的,辉煌赴死的浮雕,扭曲的血管淌出令人崇敬的微笑,这过于痛苦,这过于惊悚。 黑夜,太兴奋倦极的身体,一把沉沉不醒的安眠药,手与烟蒂,都是凶手。那个阴冷的深秋,1976年10月18日,不管周围多么明亮喧嚣,世界给他永远闭上了大门,就如同他在异乡的床上,不曾一言,只把深邃的空旷,一个大寂静,投给错愕的世界。十年炼狱,他终是完成心的历程了,他已成熟,蒂因而落,诗歌的路在天堂开通。他一直在追,他煽动燕山深处滋养的强壮翅羽,夸父一般紧追不舍,真理和诗,是他的太阳,他不断挑战,上升,靠近理想,痛苦随之加剧。他是被渴死的,累死的,烤死的。他把生命之核握得太紧,太希望它快些枝繁叶茂,他淘尽了最后一滴血,与理想同时煅烧。 那一年中国乱到极致,悲到极致。人们已经学会隐忍,把悲痛压缩,把深切的关注投向安阳。七朝古都的月光那晚有多痉挛,深埋的甲骨文发出过怎样不祥的呻吟?但这样的千年古镇担承了诗人的死,也算得其所,诗人不会被摧毁,多年之后琥珀永远是琥珀。 在迷幻的最后时刻,我愿意相信,诗人一定是拉住一棵一棵的玉米翻山越岭,回到三十年不曾走动的故乡,热河塞外古镇凤山了。那也是我的家。接天连叶的玉米高粱,他称为青纱帐,犹如俄罗斯的白桦,承担灵魂的最后居所。 烟色穿过1919年9月黄绿的青纱帐,落在丰宁县城凤山赭黄的旧街,注视着石桥东胡同一家青砖黛瓦的朴素民居,穿长袍的人们,焦急地等待一个婴儿的降生。这一等近二十年,上天考验了老两口的耐心,注定送来不平凡的儿子。里尔克说“他的母亲当初怎样不孕,后来却分娩了一切。”那个娃娃分明在子宫里酝酿多年,早长出健壮的手臂,高贵而叛逆的心灵,一旦醒来,就注定传奇。 他的生亦如他的死,民国八年,世界乱到极致,悲到极致。而塞外小镇还略显平静,还算美丽的初秋,9月2日,他的哭声引起了震动,因他是县城教育局长和民国女子小学校长的老来子。且他一亮相又惊倒了众人,脐带在背上缠出大大的十字,这状况一如衔玉而生的宝哥哥,总是大有来历的。文曲星下界,还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众人以升官以发财以这个孩子哈哈哈祝贺。小川也认可这种臆测,在《老家》的诗里说,“就凭这一点,我更被人敬重。”在避难北平时,少年的心也许对着大门许诺,这里将来会写上他的名字。“原无野老泪,曾有少年狂。”那十字架是翅膀,亦是绳结,他飞得很高,然而越高,束缚越紧,只有死亡令他身轻如燕。 郭小川父辈、祖父辈及曾祖母(前排坐者郭小川曾祖母郭袁氏,后排站立者左一郭小川父郭寿麒) 2. 死亡不是绝对性的毁灭,是另一种行走,有如奔流的泉水。我们看到暗黑,而他的面前是华光,是缓缓流淌的锡拉塔喇河,金黄的山谷,石桥,瓦屋,木门,纸窗,祖父的老杏树。家乡喊他许久了。喊儿回家一定是在午夜,在山头在河边放开了喊,划破长空,刺破行者的梦,青纱帐在暖风里摇曳,妈妈在桥头悠长地笑,他叫着故乡的乳名落下来,拨掉门楼上瑟瑟的苔花,变成了母亲的孩子。 那一瞬的绮丽不属于人世,只有迷界的小川独造了那种美,灰瓦飞檐的回旋曲,砖雕的叹息,老石狮子的沉思,还是他的蕴涵贵气的沧桑古街,两百多年的老县城,14年童年,两年县长,他钻过最阔气的青纱帐,也穿过最窄小的老胡同。最显眼是雍正年的古戏楼。唱过戏,杀过人,重要的是,一个诗人站在上面喊出过正义的声音,我多年后听到了,塞外横亘的黄草川深处,我触摸到两枚琥珀,古镇和诗人。 但是我越迷恋古镇,越有一点不解。小川近三十年不回故乡,干校孤独受辱的日子,为什么不让老家暖暖飘零的心?且除了短小的《热河曲》《老家》外,亦很少写故乡,青纱帐是作为甘蔗林的对比。他走边塞赴厦门上兴安岭,写出那么精彩的边塞诗与厦门风,就是少有塞北土城子。我试图在诗里找寻答案。“长城外生我养我的小镇,在滚滚的风沙中是不是,比在我小的时候更坚毅?”他问过。“住在家乡的时候,家乡就是最美丽的,当需要离开家乡的时候,祖国的每块土地都会使一个爱国者感动神奇。”或许故乡根本无须介意,诗人具有博爱之心,且哪个失意的孩子愿意向母亲暴露伤痛? 诗人未必没有故乡与异乡的纠葛,奈何诗人就是猎手,要不停地行走,远离故乡,让心疼起来,对故乡深沉的思念,就在他乡苏醒。于是故乡像山脉,像废墟,像无数的花朵来到了,狩猎和故乡之间有多远的距离,都可以由诗歌来填满。然而故乡与异乡,末了,都安放不下他饥渴焦虑的诗魂,无法度他攀跃诗歌的高山。那具终极焦色的凹痕,是他挣扎的天问。小川,小镇,和我,到底谁该惆怅呢? 郭小川、杜惠夫妇与孩子 |
最新文章
- 04-27健康中国行|燕赵名家走进美
- 04-25【铁色之旅】春风渡我归流年
- 04-25永定河流域官厅水文化研学基
- 04-24传承创新发展非遗传承人胡凌
- 04-23防灾预警理念先行访发明家高
- 04-23刘剑新:“回望,是为了更好
- 04-22明湖画韵 情系老兵 摄影纪实
- 04-20为百姓分忧解难“春雨工程”
- 04-18无限诗情乘青少一颗赤心系家
- 04-184.23世界读书日:石家庄市新
- 04-17烈士碧血洒挂云英名长在祭拜
- 04-10河北省冀南商会召开联席会促
- 04-09第九届中国国际绿色能源与节
- 04-07畅享田园新生活第三届桃花旅
- 04-05河北省优化营商领导小组办公
最新图片
最新帖子
- 03-24阳春三月
- 12-23杨华诗歌十首
- 12-21变了,我的家乡
- 12-18手机摄影:冬雪八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