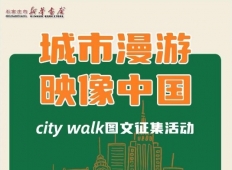尘封的农耕文化——蔚州青砂器(上篇)
文/若愚
一、
当一种农业文化被岁月尘封以后,那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代替了旧的耕作方式,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农业文化也被历史抛弃了。人们应该庆幸这种抛弃,这是一种辩证法的“扬弃”。没有这种抛弃,社会就不会进步。但是,尘封已久的东西往往是人们最最怀念的对象,蔚州青砂器正是这样一种被人们从火热的农家土屋里扔进历史尘埃中的带着农耕文化的历史产物。人们抛弃了它,却又怀念它,因为蔚州青砂器明显带着蔚州几千年农业社会的印痕,融入了祖祖辈辈农民们的火热生活和悲苦辛酸。它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视野,却在人们的思想里闪着璀璨的光芒,被老一辈农民们当做永不厌烦的历史故事讲给后人们听。 蔚州青砂器是用沉积在古老河床中的一种叫做“矸子泥”做成的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生活器皿,是被老蔚州人多少年多少代当做锅碗瓢勺甚至拉屎尿尿来使用的家俬。蔚州是我国最早就有先民生存繁衍的地区之一,他们也是华夏子孙中最具优良传统的人群之一。亿万年前,古老的桑干河盆地沉积以后,在蔚州小盆地里留下了一条母亲河——壶流河,它汇集了来自金河口、松子口、石门峪和平舒邑境内山川等众多的河流和泉水,形成一条仅仅几十公里长的汹涌河流,同样也汇集着这一带先民们的智慧和思想。壶流河两岸水草充盈,土地肥沃,最利于先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早在仰韶前期、后期、龙山时代,乃至夏和早商时期,蔚州的先民们就集中在壶流河两岸。那时,种植农业和手工业就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制陶业伴随着农业、牧业的发展而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蔚州大地上出土了大量陶器,主要有盆、甑、壶、鼎足、红顶钵、罐、瓮、圜体钵、小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等中华大地中并不少见的陶制品。仰韶后期,蔚州制陶业又放异彩,主要有鬲、斝、盉、豆、深腹盆、碗等,彩陶制作也达到一定水准。它们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那时这种类众多的陶器产品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底层老百姓由于社会地位的卑微和经济收入的微不足道,还不可能家家拥有一件心满意足的陶器用品。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在壶流河两岸放牧、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农牧业生产劳动之余,发现了沉积在沟壑中和河床里的“矸子泥”。矸子泥和人们祖祖辈辈种植的谷黍颜色大致相同,甚至和谷黍比起来还略略发白,人们欣赏这种上苍带给他们的特殊泥土。矸子泥带着淡淡的清香,和黄土地比起来,更具诱人的芬芳。农作空闲,有人把矸子泥和着壶流河水柔和成泥块,捏成“盆、碗、锅”的形状,代替陶器制品来使用。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普及,人们又把矸子泥块反复揉搓,使矸子泥更具韧性。矸子泥用水搅成泥块,变成黑褐色,人们就效仿古人制陶的方法,把变色的矸子泥块捏成“钵、甑、罐、壶”的形状,用来盛放粮食和各种杂物。
各种用矸子泥做成的器皿毕竟是泥土,遇水而化。人们从古人制作陶器的方法中得到启示之后,就用柴草和秸秆来烧制,在烈烈的火堆中,矸子泥渐渐变成灰色和褐色交杂的器物,但和古老的陶器制品比起来,还很不如意。随着日月的推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反复试验。有人在土崖上挖出了窑洞,并在窑洞中搭建了灶台,在灶台上挖出三、四尺的柴坑,放上柴草秸秆,把事先捏成的器皿坯子晾干后放在上面,盖上跟灶坑大小一样的泥制“锅盖”,点燃柴草,经一个时辰左右,“锅碗瓢勺”就烧成了。出窑后的土质器皿,果然大不相同,不仅盛水不漏,而且更具普遍的实用价值。人们不仅居家使用这类制品,还把这种制品带到田间地头,用来盛放打尖的干粮和稀饭。随着煤炭的开采,人们开始用煤炭烧制,使这种矸子泥制品更加坚硬,百姓们给它起了一个不俗的名字,叫“青砂器”。青砂器说到底,跟其他陶制品一样,都是泥土和烈火的结合物,因为烈火让泥土发生了质的变化。
青砂器的日趋成熟,是社会的进步。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相信这是神的指引,在庆幸之余,人们围着窑坑里越千度的烈烈火焰,载歌载舞。火焰把每一个农业劳动者的脸颊照耀得斑斑驳驳,让那种发自内心的欢乐和喜悦更加绚丽多彩。人们宰杀了牛羊,供奉了鸡鸭鱼肉和自家出产的土特产,祭拜上苍赐给他们的财富——青砂器。有古辞云:茫茫众象,迷离上古之望。楚有东皇,统天下洪荒。俯首为拜,酹之以椒浆。成礼会鼓,传芭代舞,尽沧桑。人们敬奉的不是神灵,奏响的也不是楚风韶乐,而是颇具特色的蔚州秧歌,颇具地方风情的秧歌也是伴随着农业生产和青砂器产生的。秧歌调和其中质朴的歌词饱含着当地人们的土语方言和满怀的激情,人们用最朴实的方式颂扬古老蔚州悠久的农耕文化。与其说,蔚州青砂器是上苍赐给蔚州人的特殊礼品,不如说蔚州青砂器是蔚州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存共享的特殊文化。后来人们把青砂器作坊搬到村庄附近,开始大规模生产。青砂器带给蔚州人是生活上的便利和精神上的快乐。土炕、灶台、青砂器构成一幅带着地域风情的蔚州农业社会历史画卷。
二、
专家们推断,蔚州青砂器产生的年代约在六百年前。那时正是封建王朝——明代建立伊始,当时全国战乱刚刚平息,蔚州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客观地说,蔚州青砂器并没有确切的产生年代,至少说还没有哪一家权威机构用确凿的证据认定蔚州青砂器确切的产生年代。但可以说,它是蔚州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孕育而出的带着地域特色的文化产物,而明代正是给予青砂器从孕育到成熟的一个关键时期。随着洪武、永乐两次大移民运动,全国各地大量军户、民户涌入蔚州,蔚州仅存的少量居民也被朝廷部分迁出,从而形成了蔚州居民大融合的历史局面,这给蔚州青砂器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蔚州青砂器像一枝绚丽的历史文化花朵盛开在蔚州广袤的山川大地上。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器皿的问世,蔚州青砂器却被重重地埋上了历史尘埃。
青砂器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最实用的土产之一。人们不祈求定窑的绚丽,也不仰望钧瓷的高贵,人们最喜爱从泥土中产生的本土文化。蔚州有一首古老民谣:老婆老汉睡热炕,睡不着来就打仗,你拿刀来我拿枪,一直打到大天亮。真切地记录了蔚州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历史原貌。那时,尽管官家令迁外地居民入蔚,可蔚州大地仍然居民稀少,不仅官府号令发展人口,老百姓更是祈求人丁兴旺。人们在各自的居住地按着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方位建立村堡和寺庙。他们白天耕作,晚上发展人口。能生育的青年人自不必说,老年人在血干精尽之后,也痴盼多生几个孩子。因此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民谣。民谣虽然有些戏谑,但确是人们繁衍生息的必经之路。青砂器是伴随人口增长而发展起来的。到清朝中期,蔚州青砂器发展到顶峰,共和国诞生之初,青砂器早就成为老蔚州人家家户户必备的主要生活器皿。
蔚州的历史很长。自商汤建立代国,汉代有了代王城,历经多少代。再后来代成君将城移至开阳堡,废代王城。王城老百姓是不能随便出入的,蔚州人更期盼有自己的城郭,德庆侯廖允中顺时应命,在蔚州壶流河中段围土造城,蔚州人才有了自己的经济文化中心。青砂器在蔚州城有了一席之地,随之成为当时自然经济市面上最抢眼的土产品之一。青砂器开始进入官吏、商贾的殿堂。在寒冷的冬季,富庶人家用青砂器炖一锅羊肉汤,妻妾陪着,明窗亮几,看那窗外飘雪。贫寒小民,一年四季,离不开砂锅,煮的是辛劳和悲苦。寒酸的读书人,不管刮风下雨,围着火盆,饮酒作诗,摇头晃脑。最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乞讨者们,也会在夜半三更,用砂锅熬一碗清汤暖暖身子。但是青砂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夯土打造的土城经历了太平、战乱、再太平,青砂器同样打碎了再捏造,伴随蔚州人走过了千百年的岁月。历史的车轮走进明代后,蔚州州指挥史周房将军号令土城万千军民烧砖甃石,在土城内外垒砖砌石,筑造铁城。铁城并非一劳永逸,它经历了战火的焚烧和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如今早已残缺不全,但给后人们留下断蛇般的老蔚州城,让后人们能有一个发思古之幽情的想象空间。历史的烟云散去,人去城废,物是人非,可老百姓居家使用青砂器的历史没有变。人口多了,青砂器自然成了普通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日用品之一。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每逢三六九集市,老州城南北大街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蔚州人自家产出的农产品,其中不乏大量的多品种的青砂器。其中有成套的大小砂锅、砂瓢。成套砂锅当然是为人口多少和烹制不同食品而特制的。砂瓢人们一般习惯叫“砂吊子”。砂吊子有两种,一种带把儿,叫“水舀”。一种没把儿,叫“尿吊子”。尿吊子是女人们夜间接尿用的。青砂匠人们又研制出青砂尿罐(chan)子,是尿吊子的配套产品。尿多了,就倒在尿罐(chan)子里,并把尿吊子盖在尿罐(chan)子上,骚味不至于溢出。青砂器是随时应运而生的,蔚州“石北也”,地处寒冷地带,早年冬季多在零下三十多度,老百姓缺衣少食,在热炕头上的被窝里解小手,不仅为了方便,也为了不被寒气伤了身子。由于“其民羯羠不均”,暖阁貂被的大族人家开始并不习惯使用这种尿吊子,但随着尿吊子的普遍使用,大户人家的女人们也开始使用这种带着“荒诞”意味的尿吊子。可见尿吊子的好处之多。
砂吊子方便了裹脚的女人们,男人们也有自己方便的砂器。那是一种特意为男人们准备的“夜壶”。夜壶“肚大量宽”,上面一个小小提梁儿,侧边一个翻口,边沿光滑,男人们夜里溺尿(sui),屌子塞进侧口里即可,具有“轻松愉快”的排泄功能。完事后提溜着放在炕沿帮子下面,以备下次使用。炕沿帮下就是灶台,人们还没起炕,就把大号砂锅撴好了,点着柴火,焖出香喷喷的小米饭,然后放上中号砂锅,熬一锅山药萝卜的大烩菜。老百姓们虽然粗茶淡饭,寒门小屋,但也过得热热闹闹。五明头上两口子炕头上“打仗”也养足了精神。早先年农户们娶媳妇,没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可以,但没有一套高品质的青砂器是不行的。不仅新媳妇不上炕,老丈母娘也不让你。数过老蔚州八百古村落,哪家哪户没有几件像样的青砂器?
老蔚州的青砂匠人们真是心细如丝。最先解决的还是吃饭问题,青砂匠人们把砂锅做成大小不一的套锅。大的脸盆大小,小的巴掌大小。农户们用大砂锅焖干饭,那中等砂锅还可用来熬小米稀饭,是女人坐月子和病号们疗养身子最好器物。青砂锅子熬出的稀饭是最养人的,不论大户人家,还是窄门小户都是爱不释手。小砂锅可用来炝辣椒、泼油腌菜。人口多了,打下的粮食也多了,青砂匠人们独出心裁,用矸子泥制作成一种极妙的小酒壶,叫“酒嗉子”,不仅有钱人围着火炉,用来煮着烧酒,哼着小曲。小户人家的男人们在寒冷的冬天也暖一壶小酒喝喝,驱驱寒气,打孩子骂女人也有了底气。富光景过得畅快,穷日子过得艰难,但有了青砂器,各有各的快乐。最是私塾里的教书老学究,哄着几个顽童,在桌上的小火炉里,煮一壶老酒,摇头晃脑,之乎者也,被顽童们打闹时碰坏烧酒壶子也是常有的事情。盛夏季节,庄户们在地里光膀子佣工锄地,杵着锄把子仰望烈日当头,忽然地主婆子提着砂凉罐把冷水饭送到田间地头,苦力们稀里哗啦喝两碗冷水饭,躺在绿荫树下,歇歇身子,听听鸟叫,也是一种不是享受的享受。
因此说,青砂器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青砂器是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人口的增长又给青砂器带来更大的需求。这一切都说明,青砂器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青砂器中所隐含的文化素养恰恰佐证了整个农耕社会的发展过程。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愚还是一个学生,暑期到辛庄砖瓦厂里干活,叫勤工俭学。午休时忽见庄稼地里冒着青烟,那青烟冲天而上。怀着好奇心,穿过田间小路朝冒烟的地方跑去。汗水流下脑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火红的熔炉。问了旁边师傅,才知是烧制青砂器的作坊。那火炉缝隙里冒着长长的火舌,把人们烤得满脸通红,近处却看不见青烟了。师傅们都光着膀子正在出窑,他们用脏兮兮的手巾擦拭着汗水,脸上青一片白一片,像没有烧好的青砂次品。旁边码放着整齐的用草葽子拴着的青砂壶。炉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师傅们扯开裤裆,朝着火炉旁边撒尿,热气霎时把尿液变成了蒸汽。
师傅们指着山一样的青砂成品说,那是煎熬中草药的砂壶。愚也是农民的儿子,父亲从解放初期战争结束后来蔚州工作,家里也是用的老蔚州的青砂器。换句话说,愚也是吃砂锅熬制的小米稀饭长大的。在愚的记忆里,青砂器对愚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师傅见愚死盯盯瞅着砂壶,就问,你家有病人?愚反口说,你家才有病人哩!那师傅说,小东西!怕你是干部家子弟吧?有病吃洋药片子,俺家祖祖辈辈却是用这家俬熬药哩!直到此时,愚才知道这种高梁儿、长嘴儿的玩意并不是夜壶,而是熬药的药壶。因为那细长的砂嘴子是根本塞不进屌子的!
原来“矸子泥”经过烧制后,其分子结构发生了微妙变化,里面含着多种对人体有利的微量元素。老蔚州人统称“药茶壶”,渐渐煎药成了主要功能。多少年来,用蔚州的青砂壶煎熬中草药,治好了普天下数不清的病人。很多人病入膏肓,用其它器皿熬制草药,不得见效。用青砂壶熬了药汁,竟然起死回生,真是不可思议。于是,师傅们讲述了一个古老故事,证明青砂药壶的好处,也证明青砂器名扬天下的确凿事实。历经多少年,传说得神乎其神。
话说清乾隆年间,壶流河北岸一位耄耋老人肩挑一担药茶壶,翻山越岭,过黄帝城、走妫州、翻八达岭、进燕山,颤颤悠悠不远千里,来到北京皇城根下。那日晨曦刚刚升起,老人叫卖了一天,晌午只吃了一碗炸酱面,一口水没喝,日落西山,一担药壶一个也没卖出。从早到晚,却见一穿金戴银之阔少,往来数遍,问了几次价码。老汉如实回答,一块银元一个。阔少擤擤鼻子说,家母得了顽症,吃遍京城名医,均不见好转。有人说是没用好壶的缘故。于是,遍访天下名壶,什么景泰蓝、青花瓷、紫砂器,金银器皿,个个用来煎药,也不见效果。今见泥捏的药壶,有心买去试试,又嫌价钱太高,捋捋袖子扬长而去。老汉望着背影说,不贵哩!只你佬一碗燕窝汤的价格!阔少理也不理,远远去了。
老汉城墙根里风餐露宿,歇息一夜。第二天日落仍然没卖出一个,一气之下,把一担近二百个药壶摔了个粉碎。恰恰一个轱辘到城壕边上,被杂草卡住,没有破碎。老汉由于积劳成疾,日间受了冷落,夜间感了风寒,打起摆子来。太阳出来,自个开方,药铺里抓了几味中药,不过是柴胡、防风、细辛之类的解表药,捡起未碎的药壶,墙根拾柴火熬了药汁,几口喝了,墙根睡了一夜,出一身臭汗,第二天安然无恙。团了绳索,拿了扁担就要出城。且那晨曦映照,老汉高高的鼻梁,黑黑的脸庞,就像风蚀雨洒过的青砂壶一样。
那阔少回家巧遇一在蔚州做买卖的朋友说起蔚州药壶的好处,又听说老汉突然发病熬药的经过。急忙出来寻找卖壶老汉,见老汉把一担药壶都像响炮一样摔碎了。真是后悔莫及,悔不当初,掐掐自个大腿,就说要买老汉手里仅剩的药壶。老汉说,不多不少,五百个光洋。阔少有的是钱,为家母治病心切,只好忍痛腰中掏出五百元一张银票,递给老汉。老汉二话不说,怀揣了银票,指着脚下药壶说,拿去吧!忽被一太监拦住去路。
阔少家母用蔚州青砂药壶煎了几扎中药,病情渐渐好转。过了几日,再来原处寻找老汉,闲汉们嘲笑说,早被乾隆请进宫里了。原来那青砂器不比金银铜器,最受不得急火。阔少急于为母治病,多添了些木炭,就将壶底子烧塌了。回头想多买几个留作备用,没想到老汉一怒之下,断了他的念想。
传说毕竟是传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但这个故事说明,各种药壶都有明显的缺陷,用铜锡壶熬药是不可取的。因为铜锡是有毒的。而蔚州青砂器汇集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它是大自然的结晶。日落回城,火窑边码放着一垛矸子泥做的火窜,跟火炉一样,是一种专门架在火盆内烧火的器具。火窜没有烧制,也是用矸子泥手工捏成。泛着矸子泥发白的本色。师傅们说,它是蔚州青砂器的孪生兄弟。有了壶,而没有架火的工具,那壶还有什么用?多少年来,老蔚州人家家户户炕上都有一个黄泥捏的火盆,这种火盆没经烧制,厚而笨重,盆膛内放些未烧尽柴灰,用来烘烤屋子,自从有了火窜、砂器,火盆就成了配套物件,具有取暖和烹饪双重功能。火窜撴在火盆上,砂锅架在火窜上,其构成并不简单。
当师傅们把一炉炉青砂器从烈火中拾掇出来,他们满身灰尘,与山一样的青砂器站在一起,早已分不出哪个是青砂器?哪个是师傅?因为蔚州青砂器原本就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师傅们笑呵呵跟愚说,甭干砖厂那苦力活了,没个豆儿大?就跟俺哥们学捏壶吧!愚回答,不学那耍尿泥的手艺。
四、
蔚州青砂器不仅是底层老百姓的专属物品,也是官僚阶层士大夫的心爱之物。自从耄耋老汉摔壶的故事传开之后,京城八旗望族,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纷至沓来。人们跋山涉水来到蔚州采买蔚州的青砂器。一时千里驼队,夜伏昼出,铃声响遍山谷。有的富商竟然在京城前门大珊栏开办了老蔚州青砂器专卖门市。门前也挂起了譬如“砂器庄”、“青砂行”之类的挑帘。使蔚州青砂器一时暴涨千金,而青砂器的故乡蔚州也日渐缺货,一壶难求,工匠们日夜劳作,忙得不亦乐乎。
自从被乾隆皇帝请进宫去,耄耋老汉日日锦衣玉食,被朝廷供奉着。老汉受不了荣华富贵,一日跟乾隆皇帝说,陛下若怜爱老奴,不如放老奴出宫去吧。老汉我回乡之后,当效犬马之劳,为陛下日夜赶制药壶,只是祈盼陛下及皇妃们不再有恙,个个身健如牛哩。说罢匍匐在地,叩头不止。乾隆皇帝笑笑说,朕倒是不必健壮如牛,尔却是要好好保重哩!不然哪个为朕转运这易碎的青砂器哩!说罢,给老汉包裹了银两,给还绳索扁担。老汉也不言谢,忙穿了龌龊衣裳回乡去了。哪知老汉是熟透的老菜瓜,回乡不几日,死在青砂器作坊里。乾隆感怀万千,写下一首《姜女祠》:凄风秃树吼斜阳,尚作悲声配国殇,千古无心夸节义,一生有死为纲常。可惜,不是专为老汉而作。
俗话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蔚州青砂器却不是这样,而是“宁为瓦全,不为玉碎”。蔚州青砂器原本是泥土做成的物件,被烈火煅烧之后,发出黑金般的光芒,黑里透着湛蓝,湛蓝里泛着青光。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像堂堂正人君子一样,易折不易损。摔碎了身子也绽放着光彩。诗仙李白曾作诗云: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渐渐,蔚州青砂器跨过江南,进入塞北,走进陇西,飞越渤海。有多少“健儿”牺牲在万里征途上,最终到达终点的是那些无畏的“勇士”们,它们给千家万户送去了美味佳肴,送去了幸福和安康。更重要的是,它们把古老蔚州的农耕文化传遍了祖国大地。
愚也在逝去的记忆里寻找青砂器蕴含的浓厚民俗文化。记得在很久以前,那时愚刚满七岁,母亲用砂锅熬制了老蔚州南坡北壑出产的金灿灿的小米粥。人们刚刚从三年暂时困难中解脱出来,很多人还不富裕,农民更穷苦了。小米粥熬得粘稠有度,香甜可口。由于放在锅灶上时间长,母亲用坏了十几个砂锅。那破碎的砂锅片儿就散放在屋檐下台阶上,被比愚年龄还大的老鸡们扑腾着凿啄上面残存的米粒。那副画卷并不是“丰年留客足鸡豚”,而是盼望“柳暗花明又一村”。后来,母亲不用灶堂,而是改用矸子泥素做的“火窜”了。火窜用炭很少,尤其在夏天使唤能节省不少燃料。火窜火焰小,砂锅子撴在上面不至于烧坏。
出去玩耍,偶到前院老邻居张老太太家中。张老太太孤身一人,梳着姥姥头,脑后发丝团一个球状,上面罩着黑线网子,头发上还抹了杏子油,那头发乌黑如墨,丝丝闪着光亮,下面裹着小脚,穿着大裤裆裤子,袄儿是偏大襟绣了滚边的,俨然一个“富贵”的老蔚州人。其实,她家里很穷,没有什么收入,只靠生产队救济过活。男人早年被土匪绑了票,单苗儿子上南山打游击也被州官砍了脑袋。张老太太干净利索,不像死了男人和儿子。
张老太太一人住着三间土屋,屋顶很低,像山一样压着头顶。只是土炕上脱落的漆盘里撴着矸子泥做的火窜,没有那笨重的火盆,漆盘只有城里才有,农村是很少见的。火窜里有几块烧透的红枣般大小的炭火,火窜上架着砂锅。土屋被东西两侧的州衙门和耶稣堂夹在中间。张老太太见愚目不转睛看着砂锅,就问,小子!看啥哩?愚想起母亲的砂锅,多有所思。张老太太说,俺这砂锅用了二十多年了。愚想,用了二十年也不破碎?张老太太似乎看透了愚的心思,自个磨叽说,这砂锅还是俺儿上山时从集市上给俺买回的哩,嗯呀。唉……老汉死了,儿子也死了。那是愚头一回听老蔚州城里老人们讲话,当地口音里带着“嗯呀”俩字。一声“嗯呀”道出了老人一生心中的悲苦和生活的辛酸。
直到此时,愚才发现那架在火窜上的砂锅比别人家的更黑,很少用油浸过的砂锅经过积年累月,也浸入了不少的油渍。张老太太一边诉说,一边从破柜子里拿出一个柳编的盒子,打开盒子,也是一个黝黑的砂锅。张老太太一边擦拭着砂锅,一边说,这是俺太祖爷爷使用的砂锅哩。说着,拉了愚的手,到堂屋里祖宗牌位上指指点点,“那个就是俺祖太爷爷哩!”。愚看看那幅挂在黑墙上的字画。原来是一种叫做“云”的家谱。张老太太所指的名字在最上面二三行的位置,叫张什么,也看不清楚。张老太太说,俺祖上是从山西大槐树下移民过来的。“移民”二字正好说明老蔚州自汉至明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战火纷飞、地旷人稀、狐藏兔跑的荒凉景象。
当然,愚当时并没有弄明白张老太太话里的所有意思。及至而立之年,才渐渐悟出了其中含义。愚掰着书本查对张老太太所说的年份。原来张老太太祖上也是明洪武年移民到蔚,算起来也有六百年历史。张老太太的始祖生下儿子,儿子又生孙子。是孙子买回砂锅,用了几十年,留下传给后代做为纪念的。愚仔细瞅那祖传的砂锅,锅底上有微微的裂纹。张老太太说着,土炕上砂锅里的粥熬好了,张老太太款款端下砂锅,把砂锅轻轻放在地上一个玉米皮编制的小垫子上。张老太太说,这样就不怕冷地面吸掉了锅底儿。愚突然明白,母亲之所以用坏了多少个砂锅,原来正是这个原由作怪哩。这才叫“宁为瓦全,不为玉碎!”玉的坚硬是因为它的纯洁,而青砂器的纯洁正是泥土的真实。张老太太又把一个小砂锅架在火窜上,放些清水,煮了腌菜,滴几个油点,算是她的“佳肴”。那老腌菜咕嘟着水泡,香味渐渐溢出,弥漫在窄小的土屋里,总有一点泥土的味道。她一辈子没吃过好的,但吃了一辈子香的。张老太太脸色白皙,有着岁月留给她的细细皱纹,腰弯得很厉害,这都是沧桑的年轮。其实她刚刚满了四十岁。愚问,炕上那漆盘也有年份了吧?祖宗从大槐树下带来。张老太太声音不高。很明显,漆盘里记载着她和丈夫更多的故事。恰恰院里也有一棵弯腰的老槐树,荡着几簇槐花。
张老太太下身穿着白色大裆裤,上身是黑色袄,像土炕上白色的火窜上架着黑色砂锅那样隐含着泥土芬芳和火焰的热情。张老太太却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怀念。
五、
一九六五年,愚已经小学四年级了。那时四清运动即将结束。愚开始用另一种眼光观察老蔚州的青砂器了。那日,愚到同学家作业,那是老蔚州有钱人家的高屋建瓴式的宅院,青砖灰瓦,很是阔绰。同学家住在三间正房里,耳房和东西下房住着老州人们的后代。其中被定为“破落地主”的老房东就住在东耳房里。老房东也是一个老妪,年纪要比张老太太大得多,约在七十岁左右。同学悄悄告诉愚,老妪家早年是蔚州城里最大的财家之一,家产无数,金银如山。多被没收和分配给贫下中农们。老妪也没有儿女,更没有收入。只把家中偷藏的银元拿到银行里兑换,过着简朴的日子。这种不对称的兑换是需村公所开具证明的,因此老妪每次兑换现金,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同学叫她“老妪”,有一种不敬的感觉。
同学的父亲也是打游击出身,只是没有被敌人打死,当年在东岳支队当了一个小队长,多年风里来雨里去,得了严重的胃病,解放后在县人委当了一名副职领导干部。因身体不好,就在家养病,常年吃着特供。愚到同学家,总是闻到一种肉味的飘香。但不知肉味从何而来。总以为是地主婆子屋里传出来的。可那老妪脸色蜡黄,步履蹒跚,不像经常吃肉的样子。每次走过同学家屋檐下,她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留下葡挞的脚步声。正应了那句“从人屋檐过,怎敢不低头”的老话。
又一日,愚作业稍晚,同学父亲忍不得饥饿,就从大柜里取出火窜和砂锅,同样架好放在炕上的铜盘里。那火窜、砂锅跟母亲和张老太太用的一模一样。愚突然发现同学父亲的炕上还铺着厚厚的栽绒毯子。愚不得不“肃然起敬”,叫他一声大爷。大爷从橱柜里拿出早已备好的鲜嫩的羊肉疙瘩,一块一块数着数目,直到“二十”,声音戛然而止,羊肉足足有半斤之多。大爷把羊肉疙瘩码放在砂锅里,放上清水,加了花椒大料咸盐等调味品,火盆里夹了红枣大小的一堆红火炭,一个个放在火窜内,不大一会砂锅就开始咕嘟了。先是冒着微微的小泡,稍过一会,砂锅里的肉疙瘩滚起来了。那火炭渐渐失去焰火,羊肉就在砂锅里慢慢烹煮。不过半个时辰,羊肉煮熟了。大爷目不斜视,一个人吃着滚烫的鲜羊肉,不停地巴扎着嘴巴。同学就站在门口,流着哈喇子。他跟愚说,这房子和毯子以及屋内一应摆设家俬都是老妪的。
那天夜晚回到家,母亲也在砂锅里炖着肉类。见儿子回来了,母亲淡淡地说,咱家那只瘸腿的老母鸡死了。愚掐指算算,老母鸡大概活了十几年了,论岁数也该死了。不过愚还是掉了几滴眼泪,因为它一生中不知产过多少鸡蛋,而到临死还是孤身一个。母亲却惦记着给儿子补补身子,拿筷子夹出一块鸡肉咬咬说,炖了一天一夜还不烂呢。直到午夜鸡肉终于炖烂乎了。母亲从被窝里把愚叫醒说,儿啊,快快吃鸡肉。那火盆、火窜里还冒着青烟,愚翻身嘟囔几句,不吃不吃。母亲就把鸡肉放在碗里,搁在愚的被窝旁边。翌日,父亲下乡回来,母亲同样把几块鸡肉递给父亲,父亲吃了几口才问,哪来的肉?母亲说,老母鸡死了。父亲脸一下子沉下来,把筷子一扔,可知道它是咱家的有功之臣?母亲嗫嚅着回答,俺不是惦记你和儿子的身体么?
夜晚降临,愚随着父亲把鸡肉连同砂锅的碎片用麻布包裹起来,默默埋在南墙根下面,培上厚厚的泥土。与其说是祭奠老鸡的死亡,不如说是唾骂砂锅的无能。后来才懂得,砂锅的用处很大,但它是不能在同一时间里蒸煮不同样的食物的。这也是辩证法。直到此时,愚才理解了那句“莫笑农家醋酒浑”其中的另一种含义。从此以后,母亲不再使用砂锅,而是改用双耳的铁锅了。那意思并不是完全为了蒸煮老鸡。
多年以后再次见到砂锅,是在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他家的下房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青砂器。那天从农田回来,朋友父亲正盘腿坐在炕上端着酒杯,手和老树根一样。村庄有一很大的佛庙,朋友家住在大庙一侧。炕上也有一个火盆,火盆上撴着火窜,活窜上架着小号的砂锅,小砂锅里炖着羊肉疙瘩。不过,这位朋友父亲的羊肉疙瘩切得很小很小。朋友说,他父亲这个砂锅已经用了十几年了。愚看那砂锅,疵满油渍,像多少年没有刷洗过一样。朋友父亲很安详,像庙里菩萨一样,每呷一口酒,就用筷头蘸一点汤水抹在嘴唇上,放下筷子,就端详那用了多年的小砂锅。每次餐后,那小小的羊肉疙瘩基本没动。下次午餐,就把原先剩下的旧羊肉疙瘩放在这个小砂锅里重新炖热,再添些咸盐,借以提升羊肉被水冲淡后的味道。那羊肉疙瘩虽然没动,但经过多次炖煮,肉化成汤水。除了浸泡陈年的小砂锅外,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愚曾多次看到朋友父亲这样子喝酒,那形态可掬,使人不解。这老汉眼睛很亮,深的像井也似,不仅舍不得吃,而且家里存放那么多砂锅,为何偏偏就用这么一个脏兮兮的破砂锅?朋友悄悄说,俺爹就是这脾气,砂锅是他的命哩。此时,愚看到堂屋里祖宗牌位前摆放着一个青砂做成的小小转轮,那是制作青砂器的专用工具。朋友还说,他父亲并不是舍不得吃,羊肉疙瘩本来切得很大,每天端上端下,除了浸泡砂锅,其它都变作烟云,融入到天地中去了。
原来同学的父亲就是当地一位知名的青砂艺人,也是祖传的手艺,他每天要搅和超千斤的泥土,做上百件的砂坯,是智慧和体力的劳动者。愚也悄声问道,干这么重的活儿,不吃饭怎么行?朋友笑笑,父亲并不是舍不得吃,他每顿饭要吃二斤米的干饭和一盆子酸菜哩!愚终于听懂了,陶尽山中土,炕头一粒砂,多少美佳肴,香甜千万家。朋友父亲作为一名普通青砂艺人,他把上苍应该给予他的养分全部浸透在他一生为之追求的砂锅里了!而这种来自泥土中的养分是在烧制青砂器的烈火中熔炼出来的!
2018年2月12日于温馨家园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