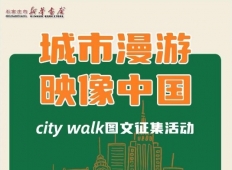上府赶考
颖川
1
天还黑乎乎的,娘便把我从晨梦中唤醒。我狼吞虎咽,吃罢一海碗金丝套蛤蟆,即挂面汤卧鸡蛋(这是冀中农家轻易吃不到的一种美食),穿上黑粗布棉袍,罩上哥哥结婚时穿过的蓝士林大褂,背上香喷喷千穗谷枣饼子,离开生我养我的庄子,跟着金九哥,步撵去保定赶考。金九哥待人忠厚,办事地道,早年在保定府做过买卖,是个有名的京剧票友,能自拉自唱,一口纯净的余派唱段《捉放曹》《击鼓骂曹》。跟他出门,爹娘一百个放心。
刚过喽正月十五,冰封的唐河开始溶化,大大小小的冰块,随着粼粼的波光,滚滚东流。我,乍一见这齐地皮儿的河流,新鲜极了,几乎忘却旅途的劳顿。我们一路之上,有说有笑,边走边吃(开始,金九哥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架不住我的一片赤诚,便和我一起受用千穗谷枣饼子)。太阳离西山,还有一竿子来高,我们便穿过飞机场,到了以水闸而著称的保定近郊的刘守庙。
我们沿着蜿蜒的府河迤逦而行,迤逦而行。有舱的渔船,无舱的货船(其中还有舳舻),竞走似的,朝我们而来。我仿佛进入一个船的世界。童年时代,咆哮的潴泷河冲决千里堤,高蠡广大田村被水包围,蛙声一片。那当儿,恰值处暑,我跟爹坐小白船,下田去爪黍子。那艄公撑篙划行的小白船,是我唯一见过的舟楫。府河这有舱无舱和首尾衔接的各色船只,把我的俩眼都看花了。
2
跨过府河大桥,穿过古老高大的城门,步入商家麇集的保定南大街。我的俩眼更不够使了。呵呵!这就是我心中仰慕的街市哟。
金九哥一直把我送进市府后街河北日报社,交给总务科长沈有年先生,才去投宿自己的故交。
沈先生是我的自然老师。这位知识渊博的达尔文,虽然离开故乡调河北日报社当了科长,但他爱生的拳拳之心依然如故。我来保定,正是接到他老的大札,报考位于南关大街的一家电力织布厂。
我在报社用过晚餐,沈先生把我领到报社招待所。招待所位于城隍庙西侧,一座朴陋的平房小院。我与几个招待员一见如故,合睡一条大炕,被褥洁净暄腾,舒服极了。他们跟我年纪相仿,都是天真烂漫的纯洁少年。钻进被窝,谁也睡不着觉,兴奋不已。他们给我绍介保定的风光,我给他们讲述乡间的故事。满炕叽叽嘎嘎,轰跑了悄悄飞来的瞌睡虫。
3
应试的那天,没等碧空的星斗全部隐去,我便钻出暖融融的被窝,草草洗了把脸,跑到城隍庙前一家刚开市的小吃店,买了两个火烧。我边吃边走,边走边吃,按照沈有年先生指引的路线,穿过一条条马路,出了南门,跨上府河大桥。我没心思欣赏桥下过往的各色船只,径直朝南关大街走去。电织厂门前,空寂无人。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心急火燎,来得忒早了。
过了个把钟头,应试的“举子们”陆续赶来。个个穿着蓝色的制服或黑色的操衣;惟有我袍子大褂,满脑袋高粱花子。然而,我不但没有遭到冷嘲,或投来的鄙夷的白眼,反而结识了一位爱说“得了吧你老”的小伙伴。他跟我同姓,名叫福禄,是本府的一位初中肄业生。我与福禄兄结识,也够祯祥的罢!
见到作文试题,我文思如潮,美丽的字眼儿们,浪花般地,朝我的笔端扑来。我要感谢鲁迅先生叶绍钧先生郁达夫先生和冰心女士,也要感谢曹雪芹大师和诗仙诗圣,以及其他文学家和诗人。倘或不曾受到他们文学艺术的熏陶和感染,我这只念过几年小学的农村土小子,焉能达到如此境界?
4
考试下来,沈先生让我去外边溜达溜达。这也恰合我意。你想呵,一个连县城都未登过的农家少年,巴不得逛逛省城。
我悠哉游哉,穿过摊点辐辏的城隍庙街,随着早春的人流,涌进保定府著名的“马号”即天华市场。这“马号”名不虚传,商号,茶馆,酒肆,饭庄,海啦!然而,一排排一家家,具有很大诱惑力的门脸儿,都吸引不住我这土小子。别说下馆子,去品尝与天津“狗不理”齐名的“白运章”的包子;连串闪光扯亮的冰糖葫芦,也舍不得买。可是,当我溜达到亚立剧场门前,看见曹芙蓉主演的戏码子,却着魔了。我从小在村里学戏,多次登台亮相,一些戏迷朋友,还夸我韵味好,“气死小金刚钻”;为此,差点儿被学校开除。我曾听戏友说,要想人前显胜,高人一筹,就得注意向名角“搂叶子”,意即学习人家的表演艺术。“砸锅卖铜,还要看看曹芙蓉”呢,何况咱腰包里有俩钱儿。再一说,住在报社吃在报社,不用花自己一个子儿,这个“搂叶子”的机会哪能错过。然而又一想,不行,绝对不行。自己这点儿盘缠,是娘含辛茹苦,纺花卖线的心血,我怎忍心把它野花喽?!败家子儿的恶名,我是不能扣到自己头上的。
我惋惜而又惋惜地走出“马号”,横穿督署大街,进了古莲池。莲池不售门票,免费供人游览。我漫步于弯曲的池畔,尽情体味仙境般的亭台楼阁。池面的冰儿尚未化通,越冬的藕儿依然躺在水底下睡大觉。但这并不令我感到遗憾。俺村的荷塘,比这也小不了多少。莫说绿绒般的荷叶,粉红的大骨朵儿,艳丽的莲花,就是清香清香的莲子,脆格英英的白藕,都不新鲜。
我跟着年长的中山服们,迈入池畔东侧开放的图书馆。其实,刚进莲池,转过迎门那座嶙峋的假山时,我就感受到它与碑林共同释放出的浓郁的文化气息。
身穿灰色列宁服的叉子眼镜走过来,满面春风地说,“借书么,小同志?”“不借不借,随便看看。”“好,好,坐下看会儿杂志罢。”我被这位大姐热情周到、彬彬有礼的服务态度深深感动,一头扎进油墨清芬的文学期刊之林,再无兴致去逛大悲阁、西大街与火车站。
5
电织厂招工揭晓,我名落孙山。都怪几何代数那不知趣的劳什子,若都是《一千难题解》上的玩意儿,我不拿它个前三名才怪呢!
沈有年先生的意思把我留下,先当招待员,以后有出息,还能当记者或编辑。我却不愿留在报社,想回去复读高小。
翌日一早,我和招待所的几位新雨洒泪而别,去报社总务科,吃过先生打来的馃子豆浆,向先生深鞠一躬,道声“再见”。便冒着料峭的春寒,独自出城,跨过大桥,沿着蜿蜒的府河河沿,渐渐地、渐渐地融入茫茫的冀中原野。
【作者附记】
这篇回忆性文字,写于1991年冬日,原载石家庄《太行文学》,收入《羽片集》(1993年花山版)。这次重新发表,作者在某些细节上作了增补。
2016年6月23日于燕斋。 |